“閩在海中”二重證據考
汪征魯
關于福建先民的產生與演化,我涉獵了許多的文獻及考古發掘報告,也陸續寫了若干雜記,其梗概大致為非洲智人之南來——閩在海中——七閩——閩越國——中原人南漸,將在以下的“汪汪夜讀”中娓娓道來。據人類細胞線粒體 DNA 的研究,非洲智人為全球人類最早的祖先,當是大概率的事實,然其如何輾轉入國中及福建,還有許多缺環,這里先談“閩在海中”。
一、“閩在海中”文獻考釋
(一)《山海經》“閩在海中”注疏
先秦文獻稱最早的福建居民為“閩”,亦可稱為閩族。“閩”后又轉化為地名。《山海經?海內南經》:“閩在海中,其西北有山,一曰閩中山在海中。”其意為:“閩族生活在海中,其西北有山,一說閩族生活區域中的山也在海中。”
后世對《山海經》的訓詁首推清代吳任臣(1632—1689)的《山海經廣注》、郝懿行(1757—1825)的《山海經箋注》、畢沅(1730— 1797)的《山海經新校正》和今人袁珂(1916—2001)的《山海經校注》。
對前文,袁珂作了兩處集解:一釋“閩在海中”,引郝懿行云:“建安郡故秦閩中郡,見《晉書?地理志》。《漢書?惠帝紀》:‘二年,立閩越君搖為東海王。’顏師古注云:‘即今泉州是其地也。’”“珂案:此泉州即今福建省福州。”我以為,郝懿行注解的:閩為建安郡、閩中郡,不確。所謂“其西北有山”,系指閩族生活區域的西北方向有山,此為福建的內陸地區,也就是秦時閩中郡、三國東吳的建安郡之大部分地區。唐人顏師古注解為泉州,唐代一度稱后來的福州地區為泉州,故袁珂認可。我以為指我國東南沿海地區當更恰當。一釋“閩中山在海中”,引吳任臣云:“何喬遠《閩書》曰:‘按謂之海中者,今閩中地有穿井辟地,多得螺蚌殼、敗槎,知洪荒之世,其山盡在海中,后人乃先后填筑之也。’”其意為:“所謂海中,是指今天挖井開地時,每每挖出海螺、海蚌外殼、朽壞的木筏,可知遠古時代,這里的山都是在海中,現在的陸地是后人填筑起來的。”[1] 我以為,遠古時代福州地區東南諸山均在海中不錯,而現在的陸地是后人填筑起來的則不然。這在后面將詳論。
(二)《山海經》的成書年代與作者考釋
上述的集解雖闡釋了若干字面上的意思,但并未確指“閩”是什么人?他們處于什么時代?這就要先追究《山海經》的成書年代與作者。對此,歷代學人做了不懈的研究。
《山海經》之名最早見于《史記?大宛列傳》:“太史公曰:《禹本紀》言:‘河出昆侖……’……故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也。”其意為:“《禹本紀》記載:‘大河源出昆侖山……’……所以言及九州山川,《尚書》的內容還比較真實,至于《禹本記》《山海經》所講到的怪物,我不太相信。”《禹本記》現已遺失,但司馬遷是看到過《禹本記》。據我看來,司馬遷至少認為,《禹本記》《山海經》及《尚書》的若干內容或出于禹夏時代,或反映了禹夏時代信息。
漢代學者大多主張夏初的伯益撰《山海經》,即夏朝初成書說。如前面提到的西漢司馬遷即有《禹本紀》《山海經》為同時之書。
東晉郭璞謂西漢劉秀(即劉歆)亦主此說。其云:“侍中、奉車都尉、光祿大夫臣秀領校秘書、讎校秘書。太常屬臣望所校《山海經》,凡三十二篇,今定為一十八篇。已定《山海經》者出于唐虞之際……禹別九州,任土作貢,而益等類物善惡,著《山海經》。”[2] 其意為:“為官侍中、奉車都尉、光祿大夫的臣下劉秀,主持秘書省的校書、校讎工作。太常屬官望所校的《山海經》,共三十二篇,今定稿為十八篇。已定稿的《山海經》產生于堯舜以后……大禹劃分了九州,依據土地的具體情況,制定貢賦的品種和數量,而伯益等區別事物的善惡,著《山海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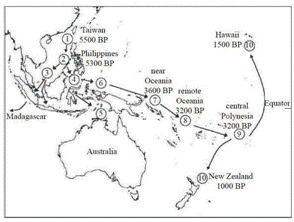
澳大利亞學者貝爾伍德提出的
“南島語族”在太平洋島嶼上的遷徙與
擴散路徑的 “Express—Train”( 快車 ) 模型
東漢王充謂 :“禹、益并治洪水,禹主治水,益主記異物,海外山表無遠不至,以所聞見作《山海經》。”[3] 其意為:“禹和伯益共同治理洪水,禹主持治水,伯益負責記錄異常之物,海外山里,無遠不至,以其所聞所見編纂了《山海經》。”
東漢趙曄謂:“(禹)遂巡行四瀆,與益、夔共謀,行到名山大澤,召其神而問之山川脈理、金玉所有、鳥獸昆蟲之類,及八方之民俗、殊國異域土地里數,使益疏而記之,故名之曰《山海經》”。[4] 其意為:“禹于是巡察了長江、黃河、濟水、淮河四條入海的河流,與益、夔共同謀劃。巡視到名山大湖,就召見當地的神仙而向他們詢問山河的脈絡條理、所蘊藏的金銀寶玉、生活于此的鳥獸昆蟲種類,以及四面八方的民族習俗,不同國家不同地區所擁有的土地里數,都讓益分別記錄下來,所以結成一書取名為《山海經》。”
由于,夏初成書說缺乏堅強的證據,宋、明以降學者多持戰國成書說。明人胡應麟謂: “《山海經》,古今語怪之祖。劉歆謂夏后伯翳(益)撰。無論其事即其文與典謨、禹貢迥不類也。余嘗疑戰國好奇之士本《穆天子傳》之文與事而侈大博極之,雜傅以汲冢《紀年》之異聞,《周書?王會》之詭物,《離騷》《天問》之遐旨,南華、鄭圃之寓言,以成此書。”[5]其意為:“《山海經》是古今以來神怪著述之祖。劉歆說是夏朝伯益撰寫的。其無論所記之事和文風與《尚書》《禹貢》都不同。我曾懷疑是戰國好奇之士依據《穆天子傳》的內容與文風并將之擴充、提高了,且兼蓄了《竹書紀年》的異聞,《周書?王會篇》的詭秘,《離騷》《天問》的遠旨,南華、鄭圃等地的寓言,寫成此書。”
宋朱熹謂:“大氐古今說《天問》者,皆本此二書(《山海經》《淮南子》)。今以文意考之,疑此二書本皆緣解此《問》而作,而此《問》之言,特戰國時俚俗相傳之語。”[6]其意為:“大抵古今人注釋楚辭《天問》,都根據《山海經》《淮南子》二書的記載。今以文意考索,疑《山海經》《淮南子》均為解釋《天問》而創作,而此《天問》之語言,乃戰國時期民間相傳的俚俗之語。”
清代以降,又以多時期層累地成書說為主。紀昀(1724—1805)謂:“惟《隋書?經籍志》云,蕭何得秦圖書,后又得《山海經》,相傳夏禹所記。其文稍異,然似皆因《列子》之說推而衍之。觀書中載夏后啟、周文王及秦、漢長沙、象郡、余暨、下嶲諸地名,斷不作于三代以上,殆周、秦間所述,而后來好異者又附益之歟?”[7] 其意為:“只有《隋書?經籍志》云,西漢蕭何得秦火所余圖書,后又得《山海經》,相傳為夏朝大禹所記。它的文字稍有不同,然都是根據《列子》的學說推衍而成。觀書中記載夏朝第二任君主啟、周朝文王及秦朝,漢代的長沙國、象郡、余暨縣、下嶲諸地名,故《山海經》決不會產生于夏、商、周三代之前,當是周、秦之間的人撰述的,后來又有好異怪之徒加以續寫。”
畢沅謂:“《五藏山經》三十四篇,實禹書。禹與伯益主名山川,定其秩祀,量其道里,類別草木鳥獸。”“海外經四篇、海內經四篇,周秦所述也。”西漢“劉秀(即劉歆)又釋而增其文,是《大荒經》以下五篇也”。于是其概述為:“《山海經》作于禹益,述于周秦。其學行于漢,明于晉。”[8]
袁珂認為:“《山海經》不是出于一手,并且也不是作于一時,是可以肯定的。”“《大荒經》四篇和《海內經》一篇成書最早,大約在戰國初年至中年;《五藏山經》和《海外經》四篇稍遲,是戰國中年以后的作品;《海內經》四篇最遲,當成于漢代初年。它們的作者是楚人,即楚國或楚地的人。”[9]
總之,現在學術界的主流看法是:由于《山海經》內部所體現出的整體性和差異性,可以推論出,《山海經》是由民間口頭文學流傳而來,人們從荒蠻的遠古時代起口耳相傳,并在一代一代的流傳過程中不斷演變增益,書稿集成于戰國之初,后歷兩漢、魏晉仍有修改增訂。應當說,這是一個宏觀的框架,其中的具體內容,在有文獻記載的商周以降部分較多得到整理與實證,而在無原始文獻或文獻稀缺的虞夏部分如“伯益撰《山海經》”“閩在海中”還缺乏有力的證據。
二、“閩在海中”曇石山文化考古資料考釋
王國維首創二重證據法。其謂:“吾輩生于今日,幸于紙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種材料,我輩固得據以補正紙上之材料,亦得證明古書之某部分全為實錄,即百家不雅馴之言亦不無表示一面之事實。此二重證據法惟在今日始得為之。”[10] 那么,是否有地下的材料,可以論證《山海經?海內南經》所謂的“閩在海中”?竊以為,答案是肯定的。
古今學者一般認為,無論是明言《山海經》為夏初伯益所撰或推測為洪荒時代的口頭文學流傳下來,其一部分內容可以追述至夏初。夏王朝紀年約為公元前 21 世紀至公元前 6 世紀,那么夏初距今為四千余年,為福建地區新石器時代晚期,具體說就是曇石山文化時期。
據近五十年來的福建考古發掘,福建地區新石器時代文化的面貌已初步廓清,“大體可以區分為兩大體系,一是面向海洋的東部體系,一是面向內陸的西部體系,這兩大體系的分野,同由閩中大山帶所造成的地區分隔,基本上是吻合的 [11]。”
(一)面向海洋的東部體系
其面向海洋的東部體系,文化類型基本為貝丘文化,可分為早中晚三期:
1.早期
早期的代表為亮島文化,其主要考古資料有《媽祖亮島島尾遺址群第三次發掘報告》[12]《馬祖列島自然環境與文化歷史研究》[13]。
對此, 楊琮認為:“ 到了距今 8300— 7000 年前新石器時代早期的后段,福州地區出現了原始社會的‘亮島文化’。這是 2011年考古工作者在馬祖列島中一個不起眼的小島——亮島上發現的。前后兩年的考古調查和發掘,共發現了四處史前時代的‘貝丘’遺址。他們在遺址中不僅發掘出土了大量的貝殼堆積,其中還有許多動物和鳥類的骨骼以及人工制作的骨器等遺物;同時還出土了一批早期的印、劃紋和涂紅的夾砂陶器殘片,也出土了一批石器工具。此外,還發現了兩座年代不同并保存有人類骨骼的墓葬。亮島遺址的這些重要的考古發現,填補了福州地區新石器時代早期歷史的空白,建構起了新石器時代早期后段的歷史文化的坐標。亮島,這座位于馬祖列島中的并不起眼的小島,遂即成為中國福州一個遠古海洋文化的名稱。”[14]
2.中期
中期的主要代表有平潭殼頭遺址,距今 6500 年至 5500 年 [15],考古資料有《福建平潭殼丘頭發掘簡報》[16]《2004 年平潭殼丘頭遺址發掘報告》[17]《殼丘頭遺址人骨觀察》[18] ;平潭西營遺址,距今 6800 至 6500 年 [19],考古資料有《1992 年福建平潭島考古調查新收獲》[20];金門島富國墩遺址,距今 6300 年至 5500 年,考古資料有《金門富國墩貝冢遺址》[21];等等。
對此,林公務認為:“殼丘頭文化遺址地處平潭島灣海岸山麓坡地上,面積不到三千平方米,是個小遺址,文化堆積較薄,且主要堆積物為貝殼,其中夾不少獸骨及部分文化遺物,灰層少見。文化內涵比較簡單,同類遺址如平潭南厝場、金門富國墩,還有粵東北的潮安陳橋等處 [22],基本上都屬于這種性質。這些遺址均地處濱海沿岸或海島上,背靠大山,面向海洋。山上的采集狩獵,海岸邊的捕撈采貝,是他們最主要的經濟活動,目前還沒有跡象表明有農業存在。”“上述諸要素所構成的殼丘頭遺存的文化內涵及其所呈現出的文化特征,除了以上所列舉的與該遺址屬于同一性質的同類遺存,如富國墩、陳橋等有相似的文化特征外,目前尚未發現于其他文化之中,是具有濃厚的地域性文化,因此,我們可以稱之為‘殼丘頭文化’。盡管迄今此類遺址所發現的點還不太多,但就這些零星的點來說,已經給我們大致指出了一個此一文化分布的空間范圍,即該文化主要分布福建中、南部及南達廣東東北部的沿海地區。”[23] 這里有兩點可注意者:一為原發性,即殼丘頭文化內涵及特征除其外延至廣東陳橋遺址外,尚未發現于其他文化中,是具有濃厚的地域性文化;二為空間分布,主要分布在福建中、南部及南達廣東東北部的沿海地區。
3.晚期
晚期的代表最典型的為曇石山文化,距今 5500 至 4000 年 [24],考古資料有十一次考古發掘報告的匯集本《曇石山遺址——福建省曇石山遺址 1954 年—2004 年發掘報告》[25]《關于福建史前文化遺存的探討》[26]《閩侯曇石山遺址發掘新收獲》[27]《曇石山遺址第十次發掘出土的哺乳動物》[28]《福建閩侯縣曇石山新石器時代遺址出土的獸骨》[29]。
曇石山文化其他重要遺址的考古發掘:福清東張遺址下層,其年代約與曇石山文化相近,考古資料有《福建東張新石器時代遺址發掘報告》[30]《福清縣東張鎮豸寺新石器時代遺址第 11—39 探方發掘報告》[31];閩侯白沙溪頭遺址下層,距今 5500 至 4000 年,考古資料有《福建閩侯白沙溪頭新石器時代遺址第一次發掘簡報》[32]《閩侯溪頭遺址第二次發掘報告》[33]。
福州地區為曇石山文化的密集區,即中心地帶,其遺址尚有閩侯莊邊山遺址下層,馬祖列島熾坪隴遺址,閩侯大坪頂遺址中層,連江縣透堡鎮館讀村黃岐遺址 3、4 層,閩侯白頭山遺址,閩清南文墩遺址,福州市區淮安遺址,福州市區浮村遺址,福州市區橫嶼遺址、閩侯縣洽浦山遺址,閩侯橋頭遺址,閩侯赤塘山遺址,閩侯鳳山遺址,閩侯牛頭山遺址,閩侯寨垱遺址,閩侯雞公山遺址,閩侯象山遺址,閩侯西塘山遺址,閩侯上街岐頭遺址,連江貴嶺遺址,連江獅山遺址,連江云居山遺址,連江崗頭山遺址,平潭蘇澳崎遺址,平潭馬鞍山遺址,平潭湖南邊遺址,等等。[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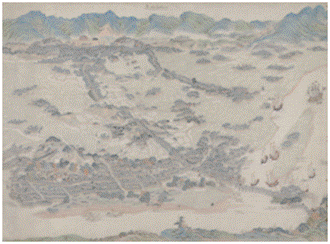
約繪于17 世紀下半葉的《福州全圖》
關于曇石山文化的生產力發展水平與社會形態,曾凡認為:“現根據這種文化的綜合分析,大致已由母系氏族過渡到父系氏族社會了。”“有了比較發達的原始農業和漁業,而這些生產部門在生活中占有相當重要的地位。各遺址中都有發現為數較多的石錛、石斧、石鐮、石刀、蚌刀、貝耜、陶網墜等。這些都是用來從事農業或漁業的一種生產工具,而且有大量而很厚的貝殼堆積。”“有了比較發達的狩獵業和畜牧業,而這些生產活動在人們的生活中同樣占有重要地位。我們在遺址中,不但發現有用于狩獵而式樣眾多的石鏃和骨鏃,而且還有為數不少的各種獸骨。這些動物骨骼,經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鑒定,計有狗、豬、豪豬、棕熊、虎、印度象、梅花鹿、水鹿、犀、牛、葉猴、鱉等。”“有了紡織業、縫紉業和制陶業的技術。根據各遺址中出土的大量陶器、陶片、紡輪和骨針等,可以得到證實。特別是制陶技術已經在慢輪修整基礎上,創作了轉動比較快速的陶輪,采用這種陶輪制作的陶器,厚薄較為均勻,器形也較為規整和精美。同時,也提高了生產效率。從其出土的數量之多,可知這種手工業在當時也是很普遍而發達的。”[35]
關于曇石山文化時期的人口數量,王銀平根據目前發現的曇石山文化時期遺址、墓葬的數量,以及遺址的占地面積(包括當時福建省內其他地區遺址)等資料進行的分析推算,得出了“福建曇石山文化時期人口規模在 13822 人左右,平均人口密度為 3 人 / 平方千米”[36] 的結論對此,楊琮認為:“我們認為如果僅從以福州地區為主的閩江下游的曇石山文化先民的人口來看,這個數字可能還比較接近。但是他所指出的是福建全域當時的人口數,顯然不夠準確了,而且可能相差甚遠。”[37] 我以為這個數字估計偏低,因為它是基于已發現的遺址、墓葬數量來分析推算的,當尚有很大數量的遺址、墓葬未被發現,姑且加上一倍,為二萬五千人。當時,在福建新石器代時代晚期,此一東部沿海型的曇石山文化是最大、最繁榮的文化,而西部的內陸型新石器時代晚期的文化就相對薄弱,以當時福建省西北部、西南部的人口統括之當亦不超過曇石山文化之人口數,姑且亦算為二萬五千人,則當時全省人口數當在五萬之內。
在與周邊地區的關系上,由于福建東南沿海地區為西部、北部大山阻擋,由于福建新石器時代進程發展相對緩慢,在曇石山文化時代其尚保有某種獨立性。對此,楊琮謂: “曇石山文化明顯是由亮島文化至殼丘頭(曇石山下層文化)一脈相承地發展起來的。在這個發展過程中并不排除它會與閩北牛鼻山文化等臨近地區的原始文化互相交流和影響,只不過這種影響是非常有限的。”[38]
(二)面向內陸的西部體系
這一地區的新石器時代文化與東部地區有本質的區別,對此由國家文物局主編《中國考古六十年?福建省》有精要的概括,其云:[39]
閩西北地區多為山間河谷的山崗遺址,相繼發掘了明溪南山、南平寶峰山、浦城牛鼻山、浦城黑巖頭、武夷山葫蘆山、武夷山梅溪崗、邵武斗米山、浦城連墩遺址、連城草營山等遺址。距今 5000—4000 年前牛鼻山文化與距今 4000—3500 前的馬嶺文化之間存在著一定的傳承關系。
牛鼻山文化在閩西、閩北分布較廣,典型遺存有南山、牛鼻山、梅溪崗下層、浦城連墩等遺址。牛鼻山遺址位于浦城縣管厝鄉黨溪村牛鼻山南坡,1989、1990 年先后兩次發掘面積 900 平方米。共清理新石器時代墓葬19 座,灰坑 8 個,出土石器、玉器、陶器等遺物 300 多件。牛鼻山文化有自己的鑇特的風格,同閩江下游及東部沿海地區的曇石山文化有明顯的差異,與毗鄰的江西、浙江等地的同時期新石器文化有相似之處。
在邵武米山遺址發現類似于干欄式房屋遺跡一處,以及一批同時期的豎穴淺坑式墓葬。出土隨葬器物有陶器、石器、玉器等。玉器隨葬是一個特別突出的發現,幾乎每墓均有,最多的一墓達 6 件,這種情況是福建以往新石器時代墓葬中所少見的。
馬嶺類型(或肩頭弄類型)處于新石器時代末期至青銅時代早期的過渡時期,相當于中原的夏代至商代早期,距今 4000 年—3500年,在光澤馬嶺、邵武斗米山上層、武夷山的葫蘆山、浦城的貓耳弄山等遺址都有發現。其以黑衣陶為主要特色,出現了甗形器、敞口尊、曲腹盆、圜底缽、魚簍罐、虎子等新的器物組合。在葫蘆山的遺址中發現了有平面呈葫蘆形、個別呈圓形或長條形的陶窯,在貓兒弄山窯群甚至出現了長達七八米的龍窯,窯中出土了黑衣陶、赭衣陶、紅衣陶和彩陶器。
這里首先要正名的是,夏王朝初年所指稱的“閩”為閩族,他們僅僅生活在今天福建的東南部瀕海地區及其近海的島嶼上。而今天福建面向內陸的西部地區被稱為“閩在海中,其西北有山”,即“閩”西北方向的山區。這一地區新石器時代晚期的典型文化是牛鼻山文化及稍后的新石器時代末期至青銅時代早期的馬嶺文化。牛鼻文化,一則有自己的風格,二則與曇石山文化有明顯的差異,三則與毗鄰的江西、浙江同時期的文化有相似之處。對后者,有學者謂:“牛鼻山類型與曇石山文化有較大的差異,而與江西樊城堆類型文化有著極其密切的聯系。”[40]又有學者謂:“在牛鼻山文化形成發展過程中,不同程度地受到過以贛鄱地區為中介的、來自長江中下游崧澤、北陰陽營、黃鱔嘴、薛家崗和屈家領文化的影響。”[41] 顯然,這一地區在夏初并不包括在閩的范圍內。
馬嶺類型文化則與牛鼻山文化有一定的傳承關系。
綜上,經二重證據考釋,可知數點:
第一,《山海經?海內南經》所載的“閩在海中”是信史,其泛指福建東南沿海新石器時代早期已有先民生活在今天近海亮島等地,中期生活在今天平潭島、金門島等地的先民;特指晚期生活在東南沿海等地的先民,故“閩”特指為新石器時代曇石山文化下的先民。其后轉化為地名。
第二,“其西北有山”系指西北內陸地區有高山,這一內陸山區在“閩”之西北方向,故其當時本身不是閩。
第三,“一曰閩中山在海中”,早期、中期,居于海島,山在海中自不待言,關于后期,據地理學家考察、研究,“冰后期氣候回暖是漸變的,由于氣溫回升,陸地冰雪消融,海面因此上升,產生了冰后期最大一次海進。福建全新世海進一般認為是距今 5000—6000年前。海進時,海面高出現今海面 2—5 米,福州盆地和漳州盆地都成為淺海灣,海灣中散布著許多島嶼,而今以‘嶼’命名的地方,如前嶼、后嶼、南嶼、臺嶼、橫嶼、厚嶼、盤嶼等,當時均為島嶼。”[42] 就今天的福州盆地而言,其時閩江的入海口退至北沙、甘蔗一帶,海水直達北峰山麓,福州盆地成了一個大海灣,露出海面的只有屏山、烏山、于山、高蓋山、大頂山、妙峰山、旗山等,其他的曇石山文化濱海地區也大致相同,故“閩中山在海中”。
第四,夏王朝伊始,中原地區進入歷史時代、即文明時代,其時福建尚處于史前時代,其大約在戰國時期才進入歷史時代。“閩”是中原夏王朝文明對福建東南沿海曇石山文化先民的稱謂。
第五,在福建歷史上新石器時代晚期,濱海亮島文化、殼兵頭文化、曇石山文化是中國最早的海洋文化,其一脈相承,相對獨立,具有獨特的個性。而西部山區的內陸文化如牛鼻山文化、馬嶺文化則比較薄弱,而且不斷為鄰近省區的文化所同化。相對而言,最早被稱為“閩”的曇石山文化先民,是福建先民最重要的代表,后來其一部分播遷海外成為南島語族的濫觴,一部分為戰國之際南下的越族所融合成為閩越族。
第六,歷代研究者始終有人堅持《三海經》發端于唐虞之際、夏初的伯益,顏師古注云“即今泉州是其地也”,吳任臣謂“知洪荒之世,其山盡在海中”,現證明均為灼見。
(原載于《炎黃縱橫》2024年第2期,作者為福建師范大學社會歷史學院教授、博導)
注:
[1] 參見袁珂《山海經校注》,北京: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3.12,第 237 頁、238 頁。
[2](夏)伯益撰、(東晉)郭璞注《山海經傳》卷 1《南山經》,經訓堂叢書匯印本。又見郝懿行《山海經箋疏?山海經敘錄》:“西漢劉秀上《山海經表》,曰:‘《山海經》者,出于唐虞之際。……禹別九州,任土出貢,而益等類物善惡,著《山海經》。”清嘉慶十四年阮氏瑯環仙館刻本。
[3]黃暉《論衡校釋》卷第十三《別通篇》,北京:中華書局出版,1990 年 2 月,第 597 頁。
[4]崔治譯注《吳越春秋》,北京:中華書局,2019 年 5 月,第 153 頁。
[5](明)王應麟《明少室山房筆叢》,上海:上海書店出版本社出版,2009 年 4 月,第 314 頁。
[6] 朱傑人等主編《朱子全書》19 冊《楚辭辯證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本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 年 9 月,第 202 頁。
[7](清)紀昀總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 年 2 月,第 3623頁。又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 142《子部 5五十二?小說家類三?同海經十八卷內府藏本》。
[8](清)畢沅《山海經新校正》,嘉慶四年(1794)經訓堂刊本。
[9]袁珂《山海經寫作的時地及篇目考》,《中華文史論叢》第 7 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年,第 171 頁。
[10]王國維《古史新證》,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8 年 4 月,第 2 頁。
[11]林公務《福建境內史前文化的基本特點及區系類型》,見福建省博物館編《福建歷史文化與博物館學研究》,福州教育出版社,1993 年3 月,第 71 頁。
[12]陳仲玉《媽祖亮島島尾遺址群第三次發掘報告》,[ 臺灣 ] 連江縣政府出版。
[13]陳仲玉、劉紹臣《馬祖列島自然環境與文化歷史研究》,[ 臺灣] 連江縣政府出版。2016 年。
[14]汪征魯、薛菁主編,楊琮撰《福州通史?先秦卷》,第 14 頁。即將由商務印書館出版。
[15]同 [14],第 124 頁。
[16]福建省博物館《福建平潭殼丘頭發掘簡報》,《考古》1991 年第 7 期。
[17]福建博物院《2004 年平潭殼丘頭遺址發掘報告》,《福建文博》2009 年第 1 期。
[18]陳盛、范雪春《殼丘頭遺址人骨觀察》,《福建文博》2021 年第 3 期。
[19]同 [14],第 127 頁。
[20]福州市文物考古工作隊、廈門大學考古專業《1992 年福建平潭島考古調查新收獲》,《考古》1995 年第 7 期。
[21]以上均見林朝棨《金門富國墩遺址》,臺灣:《考古人類學刊》,33/34 期,第 31—36 頁,1973 年。
[22]莫稚《廣東潮安的貝丘遺址》,《考古》1961 年 11 期。
[23]林公務《福建境內史前文化的基本特點及區系類型》,見福建省博物館編《福建歷史文化與博物館學研究》,福州教育出版社,1993 年3 月,第 71、72 頁。
[24]林公務《福建境內史前文化的基本特點及區系類型》,見福建省博物館編《福建歷史文化與博物館學研究》,福州教育出版社,1993 年3 月,第 74 頁。
[25]福建博物院、福建省曇石山遺址博物館編《曇石山遺址——福建省曇石山遺址 1954——2004 年發掘報告》,福州:海峽出版發行集團海峽書局,2015 年 12 月。楊琮注:報告中第 9、11頁,書中所說的第九次發掘,實際上是第十次發掘;寫到了 2010 年曇石山最后一次發掘,卻把它歸為第十次發掘,實際上是第十一次發掘。在綜合報告書標題上則應該標明是 1954—2010 年發掘報告。
[26]曾凡《關于福建史前文化遺存的探討》,《考古學報》1980 年第 3 期。
[27]陳存洗、陳龍《閩侯曇石山遺址發掘新收獲》,《福建文博》1983 年第 1 期。
[28]林鳳英《曇石山遺址第十次發掘出土的哺乳動物》,《福建文博》2012 年第 2 期。
[29]祁國琴《福建閩侯曇石山新石器時代遺址出土的獸骨》,《古脊椎動物與古代人類》第 15 卷第 4 期,1977 年 10 月。
[30]均見福建省文管會《福建東張新石器時代遺址發掘報告》,《考古》1965 年第 2 期。
[31]廈門大學人類博物館《福清縣東張鎮白豸寺新石器時代遺址第11—39 探方發掘報告》,《廈門大學學報 [ 社會科學版 ]》,1959 年第 1 期。
[32]福建省博物館《福建閩侯白沙溪頭新石器時代遺址第一次發掘簡報》,《考古》1980 年第4 期。
[33]福建省博物館《閩侯溪頭遺址第二次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84 年第 4 期。
[34]同 [14],第 300—342 頁。
[35]曾凡《從考古發現談福建史前社會的發展問題》,見福建省博物館編《福建歷史文化與博物館學研究》,福州教育出版社,1993 年 3 月,第 54 頁。
[36]王銀平:《福建曇石山文化時期人口規模及相關問題的初步研究》,《福建文博》。
[37]同 [14],第 380 頁。
[38]同 [14],第 245 頁。
[39]國家文物局主編《中國考古六十年》,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 年 9 月,第 287、288 頁。
[40]鄭輝《福建浦城牛鼻山新石器時代遺址第一、第二次發掘》,《考古學報》1996 年第 2 期。
[41]付琳《武夷山東麓地區新石器時代文化的變遷》,《南方文物》2023 年第 2 期。
[42]福建省地方志委員會編《福建省?地理志》,北京:方志出版社,2001.12,第 24 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