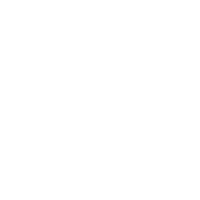求 學 篇
——楊國楨回憶錄選(二)
楊國楨
東肖教改
1958年12月,我們從龍巖馬坑來到白土。白土是東肖人民公社所在地,著名的閩西老區。1927年,中國共產黨在這里的后田村建立了閩西農村第一個黨組織。在鄧子恢、郭滴人等領導下,1928年3月4日發動了著名的“后田暴動”,成立了閩西第一支游擊隊。1929年,毛澤東、朱德率領紅四軍“紅旗越過汀江,直下龍巖上杭”,組建紅四軍第四縱隊,這支游擊隊成了一支隊的主干。這里是20世紀30年代中央革命根據地的組成部分,紅軍長征北上后,這里紅旗30年不倒,留下許多可歌可泣的故事。
白土與廈門大學頗有淵源。1951年3月至1952年2月,時值抗美援朝時期,地處海防前線的廈門屢遭空襲和炮擊,為保障正常的教學秩序和安全,廈門大學理學院4個系200余名師生內遷于此。廈門大學副教務長兼理學院院長盧嘉錫一家六口住在白土墟街南面的龍泉村,其他教師散居于溪兜村,學生分住在七公祠和菜園村。他們和當地的鄉親朝夕相處,建立了深厚的友誼。我們從馬坑到此,正值中學放假,便借住在東肖中學,師生在白土墟日都會到墟街上“改善生活”,吃一碗一角錢的龍巖清湯粉。許多老人和婦女會主動找我們聊天,說“胖胖的盧院長”(盧嘉錫)當年的親民故事。
1958年12月16日至31日,廈門大學歷史系在東肖中學開展教學整改運動。從總結一年來貫徹黨的教育方針的成績,傳達參觀全國教育展覽會及兄弟學校歷史系的教改情況開始,開展教育革命的大討論。首先肯定了一年來貫徹黨的教育方針,大搞生產勞動的完全正確,介紹四年級同學編寫《閩西人民革命史》的經驗。開展大鳴大放大字報,大字報的特點是“勢猛、面廣、量多”,第一天5000多張,第二天逼近10000張,批判資產階級的教育思想、教育制度和學術思想,對實行半工半讀、貫徹兩個三結合以及發展方向、培養目標提出看法和意見,形成運動的第一個高潮。
2012年8月22日,黃松英老師在《常常想起陳兆璋老師》一文中回憶說:
而所謂的“教改”則不同,它要求觸及靈魂,大會揭,小會批,大字報鋪天蓋地,生活上的芝麻小事也都上了大字報,教師的一舉一動都在學生的監視下,不負責任的大字報整得老師們心寒腿軟,兆璋老師和我的大字報都不少。我曾當過班主任,平時與同學接觸的機會多,很容易被挑毛病,如此“教改”弄得我們都抬不起頭。王亞南校長視察東肖時,我還當面向他告過狀。但兆璋老師很平靜,沒有一句怨言,也沒有不滿的情緒,他的淡定感染了我,我的情緒也慢慢地穩定下來。
接著,大爭大辯打擂臺,大搞教學整改方案。辯論氣氛濃厚,思想活躍,派別林立,提出二十個左右的方案,形成第二個高潮。在此基礎上,引導師生綜合整理出一份初步方案。
1959年1月6日,中共歷史系支部提出《歷史系教學整改運動總結》的報告。總結報告指出:貫徹黨的教育方針要不要實行半工半讀?對半工半讀應該如何理解?如何實行半工半讀?半工半讀會不會影教學質量?這些是整個辯論過程的主要問題。
辯論中對半工半讀有“以工為主”“以讀為主”“工讀并重”“以工為綱,以讀為主”等不同說法。許多人認為勞動與教學只能大結合,不能小結合,勞動只能改造思想,不能提高教學質量,如說:“鋤頭鋤不出秦始皇。”“參加勞動得不出文藝復興是產生在意大利的史實。”“參加勞動,專業知識沒有增長,煉鋼怎能與唐宋元明清相結合呢?”“鐵路工人寫不出高質量的鐵路史。”總結報告認為,片面強調書本上的知識,實際上是主張脫離實際,關起門來念書。我們不反對從書本上學習知識,但書本上的知識是從實踐中來的,而且還要回到實踐中去檢驗才能成為真正的知識。通過勞動雖然鋤不出秦始皇哪一年統一中國,但更重要的是懂得應該站在什么立場、用什么觀點去看待秦始皇。
面向地方是不是廈大歷史系的發展方向?這也是辯論中的主要問題之一。有人認為綜合性大學的歷史系不能只搞福建的歷史,“馬尾的地下不能發掘整個世界史”,學習的面要更寬一些,學什么史就到什么地方去聯系實際,主張“旅行大學”。——我記得教世界史的陳兆璋老師提出世界史教學要走出國門的主張,她認為:面向東南亞是廈門大學的傳統,廈門大學歷史系學生學習世界史,應安排一個學期到東南亞某地實習。這在當時,只是一個夢想。
總結報告認為,面向地方,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是貫徹執行黨的教育方針的路線問題、方向問題。不首先為地方服務,就談不上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應該明確肯定面向地方是我系的發展方向。
能否在一年內根本改變我系面貌,三年內建成共產主義歷史系,也有不同的看法。一部分人認為不可能在三年內建成共產主義歷史系,主要理由是那時還不是共產主義社會,經濟基礎還不是共產主義性質的全民所有制,學校是上層建筑,不可能是共產主義性質。報告認為,這種說法是機械唯物論,基礎決定上層,上層亦能反過來影響基礎。事實上,抗戰時期的延安抗大就是共產主義性質的學校,在黨的領導下,我們完全有可能在三年內建成共產主義的歷史系。
整改運動期間,為了迎接縣及專區檔案工作現場會議在東肖的召開,必須整理、綜合解放十年來的檔案,我們立即派出一部分師生組成工作組,包下了全部檔案材料的綜合整理工作,并為現場會議的召開準備了一個展覽會,為編寫東肖鄉解放后的歷史提供了很好的物質條件。我參加這項工作,搜集編寫《閩西老區東肖人民公社簡史》的材料。

在東肖中學教改時的合影
在總結會上,四年級同學介紹了他們在實習過程中,用三分之二時間參加勞動,僅用一個月時間進行業務學習。由于貫徹黨委、教師、學生三結合的教學方法,在一個月里不但學習了中國現代史,而且編出了17萬字的中國現代史提綱、中國現代史資料索引和閩西人民革命史解放后部分的提綱,證明勞動、教學與科學研究不但能夠結合,而且結合得很好。
總結會上,宣布整改的初步方案和當前的教學安排,一、二、三年級單科獨進,學習中國現代革命史。學習結束后放寒假,下學期開學,三個年級學生分赴閩南、閩北、閩東,編寫當地的現代革命史。
1月8日,歷史系一、二、三年級同學在東肖中學膳廳上第一課,全程19天,采用啟發報告、自習、小組討論、大班辯論、教師總結的教授方法。分成若干單元,先由老師講課,學生自習討論,再由老師總結。根據我的筆記,鄭全備講《中國共產黨的創立和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孔永松總結;張水良講《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閩西黨史研究室的陳少云講《閩西黨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總結則是:粘尚友講《紅色政權問題》,胡永樹講《三次“左”傾和機會主義路線》,葉國慶講《“左”傾錯誤的歷史根源和社會根源》;《抗日戰爭時期》(老師名字失記),陳詩啟總結;鄭全備講《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總結(老師名字失記);張水良講《國民經濟的恢復和改造到社會主義革命的基本勝利》,鄭全備總結。也就是在教中國現代史的鄭全備、張水良、孔永松老師外,還拉了中國古代史的葉國慶、粘尚友,中國近代史的陳詩啟,世界史的胡永樹等老師“客串”。

師生與革命才媽媽張龍地合影
學習期間,我們還到后田村勞動和訪問革命老媽媽張龍地等。猶記得有一天,我們走在去后田的小路上,發現一塊禁鴨碑,當即報告傅衣凌先生前來考察。
漳州編寫《閩南人民革命史》
1959年2月15日,即農歷正月初八,春節的氣氛正濃,我們班同學便組成廈門大學“閩南人民革命史”實習隊,由陳炳炎、孔永松老師帶隊開進漳州市區,入住芝山下的農校“團結樓”。
漳州市是龍溪專員公署和龍溪地委駐地。龍溪地委黨史辦公室十分重視閩南革命史料的搜集,屢次派員到外地訪問健在的在閩南領導或參加過革命工作的老領導、老同志,積累了很多口述史資料,編成檔案。這為我們的編寫做了必要的史料準備。
我們到來后,即分組到黨史辦查檔案,摘錄成大事記和史料編年,提出編寫大綱,開始編寫。我們住所附近,有一座兩層紅磚的小樓,原是美國教會學校尋源中學校長的住宅,1932年4—5月中央紅軍入漳時毛主席居住于此。樓內有7個房間,正面和東側圍墻上留有工農紅軍攻克漳州時書寫的“組織民族革命戰爭,反對帝國主義瓜分中國”“擴大紅軍”“擴大革命戰爭,實行土地革命”三條宣傳標語。1957年5月,芝山紅樓辟為閩南革命紀念館,有簡易的陳列室,供人參觀。
1959年3月13日,山西省慰問團到廈門前線慰問后,來到漳州。慰問團成員、劉胡蘭母親胡文秀等要求參觀芝山紅樓,我們班同學受命接待,并在門口集體拍照。
我們的工作得到地委領導的高度重視,4月2日,龍溪地委陳文平書記看望廈大“閩南人民革命史”實習隊全體成員,合影留念。

與龍溪地委書記陳文平合影
初稿寫出后,組織總纂小組,留下來統稿,其他同學分路到石碼、烏山等地調查訪問老紅軍、老游擊隊員、老接頭戶,記錄口述史料。
我留下來參加總纂,挑燈夜戰,半夜肚子餓,就近敲下木瓜來吃,不料發高燒,大吐大瀉到脫水,同學們趕緊把我送到龍溪第一醫院住院治療。這是我平生第一次住院,印象特別深刻。

總纂小組成員:前排左起:黃國蕩 孔永松 林再友 后排左起:陳毅明 黃成山 楊國楨
4月20日,外出調查的同學相繼回來,又按學校要求,補上了哲學課。月底,《閩南人民革命史》經地委黨史辦同志審閱認可后定稿,油印成冊,實習任務圓滿完成。
讀書集美南僑
1959年4月底,我們離開漳州,但還是沒有返回廈門大學,而是停留在與廈門島一水之隔的集美,借龍舟池畔華僑學生補習學校南僑第一樓住宿,在南僑第十六樓上課。
我根據《閩南人民革命史》的資料,在《廈門日報》5月4日第4版發表《五四運動對閩南的影響》,在《廈門日報》5月27日第4版發表《紅軍入漳史話——紀念中央紅軍進漳二十七周年》。此時,平定西藏叛亂事件的發展,成為全國人民關注的大事。配合政治學習,全班同學合力編寫大字報《西藏歷史問題介紹》。
6月7日,傳達團代會精神,進行小組討論。27日,傳達陳伯達報告,貫徹落實厚今薄古。7月1日,我根據龍溪地委黨史辦采訪到的大革命時期廈大學生羅揚才烈士的事跡,寫了《紅心閃閃》,發表在《廈門日報》7月15日第4版海燕副刊。
這年暑假,我到廈大探訪礦冶系同學,在芙蓉第二學生宿舍借宿。8月23日,正值“八二三炮戰”一周年,估計金門方面會發動炮擊,晚上要進隧道躲避,不料警報聲沒響,反而是狂風暴雨大作。我躺在床上睡覺,突然感覺有水流到頭上,以為忘了關窗戶,起來發現水從窗門縫隙噴進來,一看窗外,一棵棵大樹被臺風吹倒。24日早上起來,眼看一片狼藉,宿舍、教室屋頂全被掀起。離開宿舍,走到人類博物館,看到窗戶連框被拔掉,吹落到展覽廳內,中國猿人模型頭上滴水。走到囊螢樓旁,看到西膳廳倒塌。走出學校,返回大同路家中,從廈門港走到鷺江道,恰逢七月十九日天文大潮,海水漫入中山路,輪渡碼頭錨地設施被吹上海岸。鷺江賓館建筑工地的捆裝磚頭被臺風吹移數十米。
這是我第一次遇到的特大臺風——1959年03號臺風,廈門大學是重災區,聽說運送救災物資的卡車,單瓦片就運了60多車。
8月16—26日,文化部在鄭州召開了十一省(市、自治區)文物、博物館現場會議,提出把考古發掘技術普及到縣、社,以使人民在動土中可以隨時清理一般遺址、墓葬,一面也就可以保證專業隊伍進行重點發掘。響應號召,我試寫了一本考古發掘知識的小冊子。
9月,歷史系收本科生39人。教改后中國史教研組教師13人,世界史教師11人。9日,歷史系總支書記李金培動員學習中共八屆八中全會精神,號召大干九月,迎接國慶十周年。我們結合專業進行政治學習,出版大字報《中印邊界問題》專刊。在老師指導下,全班同學合力寫作論文《麥克馬洪線是英帝國主義侵略西藏政策的產物》,向國慶獻禮。18日,我在《新廈大》發表詩歌《倫敦的紳士們多歇一口氣!》熱情謳歌大躍進。21日,歷史系舉行第三屆學術討論會,傅衣凌先生提交的《明清之際奴變和佃農解放運動》《關于朱溫的評價》兩篇論文,引起師生的激烈爭論。不過此時我們沒有想到,一場學術批判的大風暴即將來襲。
10月25日,描寫烏山游擊戰爭的《伏擊“老虎飲”》,在《廈門日報》第3版海燕副刊上發表。11月6日,在《新廈大》發表《結合專業進行政治學習的嘗試》。
在南僑的日子,反右傾,鼓干勁運動接踵而來。11月8日,歷史系師生掀起“學經濟、趕經濟、超經濟”高潮,攻破教學薄弱環節,推動全面大躍進。
12月14日,推出廈門大學關于歷史系專業設置的五年躍進規劃:“1960年7月1日,新增中國經濟史研究室,招研究生,秋創辦中國經濟史專門化,5年內創辦中國經濟史研究所,形成中國經濟史全國專題研究中心。1961年春創辦世界近代史專門化,1962年秋,創辦南洋史專門化(與南洋研究所合作),增設東南亞史研究室,5年內創辦東南亞史研究所、形成東南亞史全國專題研究中心,同時成為世界的先進研究基地。1962年秋,創辦考古民族學專門化,1964年秋創辦考古專業。1964年春,創辦中國古代史專門化。”這個五年躍進規劃,除成立中國經濟史研究室外,受到政治形勢的變化、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沖擊,沒有實現。
1960年1月20日,因為印尼排華愈演愈烈,中國先后租用十多艘客輪到印尼各港口接運難僑回國,拉開了大撤僑的序幕。集美是安置難僑的地點之一,不容我們久住。湊巧福州大學第一批校舍建成,機械系、電機系和礦冶系采礦專業教職員118人、學生687人從廈大遷回福州本校。我們避免了再一次漂泊的命運,回到闊別16個月的學校。那時候我們沒有想過,廈大為創立福州大學,校長助理盧嘉錫教授調任福州大學副校長,校黨委副書記吳立奇調任福州大學黨委書記,抽調了數學、物理、化學三系教師,相當于分出一半理科,實力大損。
明清社會經濟問題“大討論”
1960年1月底春節一過,我們從集美回到學校,搬進囊螢樓。囊螢樓是廈大最早的學生宿舍,在我們之前,是外文系學生在住。樓旁的西膳廳,歷史悠久,去年八二三特大臺風時倒塌,學校在馬路對面西村擇地重建,俗稱外文食堂(今拆建為廈大西村大學城)。這個時候已是經濟困難時期的第二年,學生生活面臨新的問題,與我們一年級在校時的情景大不相同。記得在我們從馬坑撤退到白土的時候,一路上是“大豐收”的景象,田里的地瓜沒有人收,任其腐爛。離開白土的時候,就聽說浮夸虛報糧食產量,農民的口糧也被征調上繳,農民流傳順口溜“紅旗飄飄,肚子夭夭”(按:“夭”是龍巖話“餓”的發音),甚至出現餓死人的慘景。到漳州之際,我們得到通知,從1959年2月起,廈門城鎮居民糧食標準每個月減少3斤。
學生糧食定量不夠,出現吃飯少交或不交飯票的現象,為堵塞虧損,學校決定食堂下放給各系管理。我與同班同學參加外文食堂餐廳革新組,改革餐廳管理,試行無人賣飯,“吃共產主義風格的飯”,竟受到廈門大學團委的表揚和推廣。現在看來,這是一種以道德底線抵押的“阿Q精神勝利法”,無助解決口糧供應不足的問題。所以,試行一段就停止了。
1960年1月26日,《人民日報》發表《百家爭鳴和思想斗爭》,拉開了史學界批判尚鉞修正主義觀點的序幕。隨之,《光明日報》在2月2日,刊登了《堅持歷史科學的黨性原則——批判尚鉞同志“踏實鉆研與堅持真理”一文的修正主義觀點》。中國人民大學受命開展了對尚鉞的全面批判,一些學術團體和高等學校舉行各種形式的報告會、座談會、討論會,掀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批判運動。《教學與研究》1960年第1期發表的《評尚鉞同志對中國資本主義關系史的研究》,《歷史研究》發表的《尚鉞〈有關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的二三事〉一文中的二三謬誤》,斗爭矛頭指向尚鉞的“明清資本主義萌芽論”。
傅衣凌先生在明清資本主義萌芽的研究上,持有和尚鉞類似的觀點,是南方提倡“明清資本主義萌芽論”的主將。早在1958年6月,胡嘉在《歷史研究》1958年第3期上發表《評傅衣凌著明清時代社會經濟史研究論文集兩種》,對傅衣凌先生在《明清時代商人及商業資本》和《明代江南市民經濟試探》兩書中關于資本主義萌芽的論點,從社會經濟發生變化的原因、商業資本和高利貸資本在封建社會里所起的作用、雇傭勞動以及資本的原始積累四個方面質疑。因此,批判尚鉞伊始,就得到廈門大學歷史系領導的響應,認為傅先生露骨地系統地散播地主資產階級的反動學術觀點,站在資產階級立場,用唯心主義觀點來研究明清資本主義萌芽問題,在歪曲明代社會性質,歌頌資本主義產生的同時,結果也美化了封建社會和地主階級,掩蓋了階級剝削與階級對抗,進而調和或取消了階級斗爭。于是,發動了對傅先生的學術大批判。
1960年3月29日起,廈門大學歷史系舉行第四屆科學討論會,“對傅衣凌先生關于明清經濟史的論著進行了討論”。
開幕式上,歷史系總支書記李金培致辭,號召全系師生踴躍參加,“批判資產階級學術思想,繼續深入進行教育革命”。第一場大會,由青年教師柯友根作主題演講,宣讀他和李強、孔永松合寫的論文《評傅衣凌先生在明清經濟史研究中的錯誤學術觀點》,指出傅先生在有關商品生產與雇傭勞動、資本原始積累以及違反歷史唯物主義觀點的幾個問題上的錯誤。這場“大討論”是呼應中國史學界對尚鉞修正主義觀點的批判,但傅先生不是馬克思主義史學家,他的身份并不符合所謂“修正主義”即“披著馬克思主義外衣販運資產階級貨色以篡改馬克思主義”的定義,因此對他的錯誤學術觀點定性為資產階級學術思想。
在前10次的大會討論中,由于有力的政治動員,歷史系不同專業、不分年齡上臺發言的師生累計達59人次。許多老師都在大會上發言,批判傅先生的觀點。為討論會所寫的5篇批判文章和一篇討論綜述,很快就在廈大主辦的刊物《論壇》、《廈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中國經濟問題》上發表。
傅先生先后在大會上作了多次自我批判和申辯,在某些部分接受批評者的意見,修正了某些錯誤觀點,但也堅持一些看法。大會即把他的申辯稿《關于明清社會經濟若干論點的自我批判和一些待決的問題》《在中國經濟史研究中幾個問題的意見》《我對雇傭勞動的看法》,油印散發給全體師生作為“反面教材”,做進一步的批判和討論。我曾回憶說:
在那個不正常的年代,“左”的傾向壓倒一切,堅持學術觀點也是需要勇氣的。在一片“討伐”聲中,傅先生一場又一場頑強地進行答辯,每次都事先準備好發言稿,引用史料加以論證。逆境之中,保持學者的尊嚴,大家的風度。他的答辯稿,當時油印散發給全系師生作為“反面教材”。我讀了以后,為他的勇氣和博學所折服,也不知從哪里來的勇氣,站出來對某些批判言論提出不同意見。經歷這場“學術大批判”,我開始認識作為歷史學家的傅衣凌先生。
傅先生油印的申辯稿早已消失無存。幸虧當年4月在中共廈大黨委主辦的《論壇》1960年第2期發表的葉如針《歷史系開展關于中國經濟史問題討論》一文(修改后題為《關于明清社會經濟問題的討論》,發表于《光明日報》1960年5月26日《史學》雙周刊第187號),摘引了傅先生的部分申辯意見,為我們留下珍貴的資料。特轉引如下:
關于雇傭勞動,傅先生認為明代中葉以后出現有資本主義性質或資本主義萌芽性質的雇傭勞動。在明代農業上雇傭勞動的性質,他認為既不是資本主義的,也不是封建的農奴,而是適應于封建社會后期出現有帶著資本主義萌芽性質,含有自由雇傭若干特點的雇傭勞動。他說明代農業上的“長工”“短工”是孕育著有資本主義萌芽性質的雇傭勞動。傅先生引用列寧所說“另一種新的類型是農村無產階級即有份地的雇傭工人階級,這是包括無產的農民,其中有完全無地的農民,然而最典型的俄國無產階級是有份地的雇農、短工、小工……”,認為不一定要完全脫離生產資料,才能算是資本主義性質的雇傭勞動。
關于國內市場,他認為形成一個完整的國內市場的提法是不妥當的。但是,他堅持有封建性的國內市場是存在的。特別是中國自秦漢以后,即是中央集權的封建帝國,它應該有共同的經濟生活。既然是封建性的國內市場,因而也認為有統一的市場價格。他還說,封建社會前期,商業市場是為地主階級服務的,封建社會后期,商業市場既為地主也為農民服務。傅先生還提出:一,在中國歷史上有不少的生產品不是為供應本地方的需要,而是向著全國的規模發展,如松江綾布衣被天下,福建之藍甲于天下,不僅為滿足封建主的需要也為一般人的需要,這個現象如何解釋呢?二,在中國歷史上,圩集與市鎮、縣城與省城、省城與大區和首都是有經濟聯系的,不僅有商品流通,且有商人的操縱,南北商品交換也很頻繁,這種商業區域,仍然是封建制度下最合適的中世紀貿易形式。但它對于聯系全國各地經濟生活難道都沒有作用嗎?三,宋代以后中國基本上看不出封建的割據局面,這里有沒有經濟的因素呢?四,上層建筑時時為經濟基礎服務,在中國封建社會內漢代的平準均輸政策,宋代王安石市易法,這些措施與中國中央集權制的國家有無關系呢?
關于經營地主和原始富農問題,傅先生說,他過去把這些當作新東西是錯誤的,但他堅持,經營地主和原始富農在明代以后社會經濟中,在促進封建經濟的發展,特別對于封建后期商品生產的發達以及動搖自然經濟方面都起了作用。但又因為當時并不適宜于發展,所以最后又起著鞏固自然經濟的作用,加強農業與手工業的結合。經營地主的性質,傅先生認為是屬于封建性范疇的地主,但與以收取封建地租為目的的地主不同,而是從事農業生產的經營。在使用童奴之外,又雇有少量的雇工。他們的生產活動在自給之外,也有一部分為滿足市場而生產,只是這種經營地主在中國封建經濟的長期性歷史條件下,他們不是受到封建地主階級的壓迫,便是自己轉化為地主官僚階級,成為地主階級一分子。
這些駁論是否成立已不重要,我們看到的是歷史學家堅持學術觀點的可貴精神。
那時我是大三學生,響應黨的號召,也寫了“論文”參加批判,并在大會發言。內容大概是批評傅先生把以寧化黃通領導的清初閩西贛南農民起義軍建立的政權性的組織“長關”,說成是“原始蘇維埃”,把古代農民起義與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工農武裝割據”混為一談。文章沒有發表,我注意到,傅先生在1960年12月定稿、1961年出版的《明清農村經濟》一書中已將“原始蘇維埃”的說法刪除了。
大會發言“左”的傾向壓倒一切,傅先生孤軍應戰,無論如何舉證都不能過關。我認為一味否定傅先生的觀點有點過火,在討論明代中葉雇傭勞動的性質時,我站出來提出不同意見,引用毛主席《矛盾論》中關于事物內部新陳代謝由量變到質變的論述:
我們常常說“新陳代謝”。新陳代謝是宇宙間普遍的永遠不可抗拒的規律……任何事物的內部都有其新舊兩個方面的矛盾,形成一系列的曲折的斗爭。斗爭的結果,新的方面,由小變大,上升為支配的東西;舊的方面則由大變小,變成逐步歸于滅亡的東西。而一旦新的對于舊的方面取得支配地位的時候,舊事物的性質就變化為新事物的性質。由此可見,事物的性質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決定的。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起了變化,事物的性質也就隨著起變化。
在發言中不同意把“包含著全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萌芽于其中的雇傭勞動”與帶有資本主義萌芽性質的雇傭勞動等同起來的看法。這段話被收入廈門大學歷史系寫的討論綜述,作了報道。
我的發言,不符領導意圖,隨即受到反駁。沒想到的是,傅先生欣然接受,牢記于心。當明代中葉雇傭勞動的性質的討論成為公開論戰后,傅先生吸收了我的看法,引用毛主席的上述論述加以反駁,寫入《我對于明代中葉以后雇傭勞動的再認識》一文中,發表在《歷史研究》1961年第3期上。現在回想起來,這次發言讓傅先生認識了我,成為我們結緣一生的起點。
傅衣凌先生在《歷史研究》上發表的這篇文章,奠定了他在中國史學界的地位。1980年,此文被鄭天挺先生節錄收入他主編的《明清史資料》(上冊),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1981年,被收入廈門大學歷史研究所中國經濟史研究室編《中國經濟史論文集》,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1982年,傅衣凌先生將此文收入《明清社會經濟史論文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2008年3月,北京中華書局在《傅衣凌著作集》中再版了《明清社會經濟史論文集》。2010年,被收入《中華現代學術名著叢書》,由北京商務印書館出版。可惜的是,《傅衣凌著作集》再版這本書時,在該書第45頁把引用毛主席《矛盾論》的這段話誤注為“[德]卡爾·馬克思:《資本主義生產以前各形態》,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7頁”,而未加更正,令人遺憾。
野營拉練到東孚
1960年6月17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福建前線司令部發表《告臺、澎、金、馬軍民同胞書》:
臺、澎、金、馬軍民同胞們:
艾森豪威爾要到你們那里“訪問”了。來者不善,善者不來。他是美帝國主義的頭子,同過去的杜勒斯一樣,向來對你們不懷好意。一年多以前,杜勒斯到你們那里去,對你們施加壓力,要你們服從美國制造“兩個中國”的計劃,把臺灣完全淪為美國的殖民地。當時,我們打了炮,你們抵抗了美國人,杜勒斯沒有能夠如愿以償。杜勒斯雖然死了,美國并吞臺灣的心并沒有死。艾森豪威爾的政策,就是杜勒斯的政策。艾森豪威爾是我們的敵人,也是臺、澎、金、馬一切愛國同胞的敵人。
美帝國主義的名聲越來越臭。不久以前,艾森豪威爾破壞了四國政府首腦會議,遭到全世界人民的反對。亞洲許多國家的人民,受了美國很久很深的壓迫,對美國的反抗也最猛烈,艾森豪威爾這次從太平洋東邊跑到太平洋西邊來,就是為了維持美國在亞洲的侵略陣地,加強它對亞洲各國人士的壓迫。對于這么一個“瘟神”,人們是知道應當怎樣“歡迎”他的。這次艾森豪威爾宣布要“訪問”的地方,到處掀起了反對的浪潮。艾森豪威爾是硬著頭皮來的,切不要以為美帝國主義和它的走狗多么厲害。南朝鮮人民、土耳其人民起來一轟,就叫美帝國主義手忙腳亂,就把美國的兩個忠實走狗李承晚、曼德列斯趕下了臺。美國在日本駐扎了重兵,岸信介賣國政府死心塌地要跟美國訂立軍事同盟。可是日本人民不答應,一次斗爭接著一次斗爭,鬧得天翻地覆。艾森豪威爾被英勇的日本人民宣布為“不受歡迎的人”,他的“先行官”挨了一頓下馬威,他自己也吃了閉門羹。菲律賓受美國控制已久,那里的人民也已經起來反對艾森豪威爾的強盜旅行。臺、澎、金、馬的愛國同胞,你們當然不能容許艾森豪威爾在你們頭上耀武揚威。三年前,你們搗毀過臺北的美國“大使館”,這是反美愛國斗爭的光榮紀錄。當美國的忠實走狗,隨人俯仰,是不會有好下場的。我們知道,你們并不甘心忍受美國的欺侮。美國人在你們那里策動“臺灣自治”,制造反對派,已經使你們傷透腦筋。事到緊急關頭,美國人不會對他的走狗講什么義氣。李承晚、曼德列斯,就是前車之鑒。凡是跟著美國走的人,看了這種情況,能不寒心?一切有愛國心的中國人,都應當團結起來,同美國侵略者堅決斗爭。
為了支持亞洲各國人民反對艾森豪威爾強盜旅行的正義斗爭,為了支持臺、澎、金、馬愛國同胞反對艾森豪威爾強盜旅行的正義斗爭,為了表示偉大的中國人民對艾森豪威爾的蔑視和鄙視,我們決定:按照單日打炮的慣例,在6月17日艾森豪威爾到達臺灣的前夕和6月19日艾森豪威爾離開臺灣的時候,在金門前線舉行反美武裝示威,打炮“迎送”。美國的武裝力量,近來不斷向我們威脅和挑釁。我們這個決定,完全是為了向美帝國主義示威。一切不愿意屈服于美國壓力的臺、澎、金、馬愛國同胞,一定都會贊成。為了保護你們的生命安全,特此事先說明。在炮轟期間,你們務必躲在安全地帶,不要出來,以免誤傷。你們的船只,在這兩天也要注意,切勿駛進炮轟地帶,以免危險。倘若有人不遵我們勸告,甘心為虎作倀,膽敢擾亂偉大的反美武裝示威,必遭嚴懲,勿謂言之不預!
中國人民解放軍福建前線司令部
1960年6月17日
處于對敵斗爭最前沿的廈門大學民兵師聞訊立即行動起來,配合前線反美武裝大示威,積極開展民兵訓練。我班同學參加廈門大學民兵師第九營(歷史系、哲學系師生組成)的軍事野營活動,帶背包拉練,從學校出發,經梧村、江頭、高崎,過高集海堤和集杏海堤,來到島外,再經杏林、灌口到東孚公社,單程近百里,來回長途徒步行軍。同學們平生都未曾走過這么長的路,何況還帶著背包和武裝,走著走著便感覺吃力,但大家一路高唱戰歌,相互鼓勵,情緒高昂,隊形整齊,在規定的時間內到達目的地。安營扎寨后,在學習軍事知識、防空防炮演習外,還參加開發“百果山”的勞動,上山挖坑種植果樹苗。第三天,才從原路返回。
編寫《古代泉州海外交通史》
1960年7月,我們班同學來到泉州,在中共晉江地委宣傳部和中共泉州市委宣傳部直接領導下,與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館合作編寫《古代泉州海外交通史》。
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館設在開元寺內,于1959年7月15日開館,當時是全國首創和唯一的交通史博物館,此時剛滿一年。我們住在開元寺內,與東西塔相伴,主要利用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館的陳列、所藏的文獻和文物調查的資料,進行編寫。編寫過程中蒙泉州市文化局副局長許谷芬及泉州市圖書館,泉州市文管會,泉州市一中、二中,廈門大學南洋研究所諸單位的熱情指導和提供材料。
編寫工作開始不久,正值夏收夏種勞力緊張,福建省委號召各地各行各業抽調人馬下鄉支援,我們接到通知,立馬行動,于7月10日清晨4點出發,背上行李,徒步走到法石村東海人民公社中云大隊,支援夏收夏種。同時,也利用休息時間訪貧問苦,尋訪古代海外交通遺址,走進“歷史的現場”。當地農民得知我們是到泉州來編書的,熱情地把家中的古書、族譜拿出來,讓我們閱讀和抄錄,真是意外的收獲。
農忙過后,我們回到開元寺繼續編寫。由于當時任務較多,前后編寫的時間實際上只有十余天,主要是由同學們集體討論、執筆和修改,最后請王洪濤、吳文良兩位先生稍作修改補充。7月底完成《古代泉州海外交通史》(初稿),8月1日寫《編者的話》,交油印社謄印成冊,共78頁,征求意見。全書共分三編,第一編為泉州海外交通的興起(南北朝—五代),第二編為泉州海外交通的發展與繁榮(宋元),第三編為泉州海外交通形勢的變化(明清)。雖然是少年的習作,但不事浮華,比較客觀地評價古代泉州海外交通的歷史地位,與后來鼓吹“泉州是海上絲綢之路起點”之類豪言壯語,不可同日而語。可惜當時沒有得到修改出版的機會,以至“船過水無痕”,被學術史所埋沒。
(本文原載于《炎黃縱橫》雜志2024年5期,作者為廈門大學歷史系教授、博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