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官文化與中國式現代化
薛 菁
侯官文化是在福建的自然地理與社會歷史背景下,在宋明以來閩學的浸潤與觀照下,以及清朝末季這一地區中西文化激蕩交流中,形成的一支具有福建標識意義的地域文化。其既是福建土著文化與中原傳統文化不斷融合的產物,又是與西方文化不斷交流、創新的結果。作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侯官文化是西方文化中國化的產物,其所具有的愛國自強、開放包容、敦厚務實的精神特質,在中國近代史乃至中華民族復興史上占居重要地位,與中國式現代化有著內在的一致性。

所謂“現代化”,是指由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的變遷過程,是在社會分化的基礎上,以科學技術進步為先導,以工業革命和信息革命為主要內容,表現為經濟、社會、政治、文化、生態等各方面協調發展的社會變遷過程。歷史地看,歐美國家率先開啟現代化進程,即由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變遷。過去的五百年,在全世界范圍內的現代化發展的認知中,現代化就等于西方化。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指出:“資產階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又說:“它(資產階級)迫使一切民族——如果他們不想滅亡的話——采用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它迫使它們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謂文明,即變成資產者。一句話,它按照自己的面貌為自己創造出一個世界”。[1]日本思想家福澤諭吉也說:“現代世界的文明情況,要以歐洲各國和美國為最文明的國家,土耳其、中國、日本等亞洲國家為半開化的國家,而非洲和澳洲的國家算是野蠻的國家。這種說法已經成為世界的通論,不僅西洋各國人民自詡為文明,就是那些半開化和野蠻的人民也不以這種說法為侮辱……于是有的就想效仿西洋,有的就想發奮圖強以與并駕齊驅。亞洲各國有識之士的終身事業似乎只在于此。”[2]
但是,我們應該看到,西方式現代化是植根于西方文明——一個古希臘文明、古羅馬文明、基督教文明與現代工業文明的綜合體。在這一綜合體的背后,隱藏著的是文明論上的“西方中心主義”和“殖民主義”兩大傳統。上世紀兩次世界大戰的爆發,是為明證。惟其如此,有學者將西方式現代化稱為“西方侵略式現代化”,并在當前社會歷史條件下受到了來自實踐和價值等諸多方面的挑戰。在這一背景下,植根于中華文明、立足于中國國情的“中國式現代化”理論的提出,徹底打破了西方中心主義的世界觀和西方現代化理論一家獨霸的局面,拓展了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途徑選擇。其既有各國現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國情的中國特色。
近代以來,面對前所未有的劫難,英雄的中國人民在救亡圖存的道路上一次次抗爭、一次次求索,歷經百余年浴血奮戰,取得了民族獨立。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僅僅用七十余年就讓超過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全部擺脫貧困,堅持和完善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實現了中華文明五千年歷史長河中的現代化轉型。在這一轉型過程中,近代福州的知識精英發揮了重要作用。
鴉片戰爭后,福州作為“五口通商”之一,成為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窗口,涌現出以侯官人林則徐、嚴復、陳季同等為代表的翻譯家群體,他們在中國傳統經世致用的原則下,自覺研究西方、學習西方,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倡導者和實踐者,他們的譯作為近代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的現代化奠定了堅實基礎。
林則徐是近代中國“開眼看世界第一人”。早在1839年林則徐到廣州查禁鴉片時,為探訪夷情,遣人廣泛搜集廣州、澳門外國人出版的各種報刊,物色聘用翻譯人才,設立譯館,翻譯各類書報,組織幕僚翻譯英人慕瑞所著的
《世界地理大全》,并親自潤色,編成《四洲志》,成為近代中國第一部相對完整、比較系統地記載了亞洲、非洲、歐洲、美洲3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地理志書,被梁啟超稱為“新地志之嚆矢”,[3]也是魏源編著《海國圖志》的基石。正是在《海國圖志》這部著作中,魏源繼承發展了林則徐“師敵之長技以制敵”的思想主張,第一次明確提出了“師夷長技以制夷”思想,成為那個時代之空谷足音,在中國思想文化史上具有了劃時代的意義。它不僅是經世派代表人物在鴉片戰爭以后面對西學傳入所作出的理性選擇,是中國應對西方殖民者入侵的主要手段,也表明了近代中國向西方學習的思潮一開始就和愛國精神交融在一起;而且它是對19
世紀40年代前后中國社會出現的趨新思想潮流的高度概括,是對“經世致用”文化傳統的豐富和發展,[4]為后繼者開拓了一個向西方學習的新方向,是近代中國重要社會思潮——“中體西用”文化觀之先導,倡日后洋務運動之先聲,對后來維新思想的產生亦具啟發意義,成為傳統經世之學向近代新學轉化的發端。嗣后,無論是洋務自強運動,還是維新變法、民主共和甚于科學與民主思想都是“師夷長技”思想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繼續和發展。
林則徐的翻譯活動改變了明末以來西語翻譯以外國傳教士為主導的局面,開啟了國人從本國的實際需要出發,自覺、自主譯介西方新知識的時代,引發了“西學”熱潮。殆及清末,翻譯西書蔚為風氣,翻譯領域迅速擴大,除宗教、自然科學外,還有社會學、文學等方面的著作。如《清史稿》所云:“清之末葉,歐風東漸,科學日昌。同治初,設江南制造局,始譯西籍。光緒末,復設譯書局,流風所被,譯書競出,憂世俊英,群研時務。”[5]美國華裔學者張馨保如此評價林則徐:“在所有19世紀的中國政治家中,林則徐的形象和影響都超過了其他人。……比曾國藩、李鴻章早二三代人的時間,林則徐就已提倡和發動了向蠻夷學習的自強運動”。[6]林則徐當之無愧地被稱為“倡西學之始,開新學之路”第一人。
嚴復是近代中國“西學第一人”,“于中學西學皆為我國第一流人物”,是近代中國系統引進西方哲學社會科學的第一人。從1895年至1908年間,嚴復翻譯出版或發表的西學名著主要有《天演論》《原富》《群學肄言》《群己權界論》《社會通詮》《法意》《穆勒名學》《名學淺說》,內容涉及哲學、經濟學、法學、邏輯學、社會學、政治學等社會科學諸領域,約200萬字,后人稱為“嚴譯八大名著”,或“嚴譯八經”。尤其是1898年《天演論》的出版,震動全國,“風行海內”,名噪一時,給當時處在學問饑荒環境中的思想界輸送了新鮮的食糧,給正在進行救亡圖存、維新變法的知識分子提供了全新的世界觀,從根本上打開了國人的眼界,使得弱肉強食,優勝劣敗,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觀念深入人心,幾乎成為20世紀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奮起謀求救國圖強的醒世箴言。嚴復成為“介紹近世思想的第一人”,成為近代中國開啟民智的一代宗師。
嚴復通過譯述西方近代的學術文化經典,介紹和宣傳傳西方新興的資本主義的世界觀、方法論和價值觀,并在這一過程中形成了自己改造中國傳統社會、亦即中國傳統社會現代化轉型理想與主張。他“所選譯的書都是他精心研究過的”,“他均能了悉該書與中國固有文化的關系,和與中國古代學者思想的異同”。[7]
立足于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思維、以儒家傳統中的基本價值理念為基點來介紹和宣傳西方的價值觀,努力尋求中西思想的一致性,是嚴譯著作的最大特色。他模仿先秦文體,選擇“漢以前的字法句法”,力圖通過用最典雅的中文表達西方思想來影響講究文體的文人學士。在翻譯中,他或常常加入大量的“按語”以闡發自己的政治主張,有的按語之長,超過譯文;或結合中國時局對原文進行損益、改造,以使西方社會整套的富強之學在中國社會中植根,成為中國文化的一部分,因此,嚴復的譯著堪稱西學中國化的典范。他借助西方先進理論,通過譯著西方學術思想和政治學說以警世,誠如他自己所言:“意欲本之格致新理,溯源竟委,發明富強之事,造端于民。”[8]他“代表了近代中國向西方資本主義尋找真理所走到的一個有關‘世界觀’的嶄新階段,他帶給中國人以一種新的世界觀,起了空前的廣泛影響和長遠作用,這種啟蒙影響和作用不只是在戊戌時期和對改良派,更主要的更突出的是對后幾代包括毛(澤東)在內的年輕的愛國者”。[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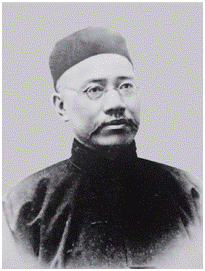
嚴復
在嚴復學術思想中,西方現代學術與中國古代經典是其兩大基石。中學是嚴復文化價值觀的基礎,他認為中學“最富礦藏,惟須改用新式機器發掘陶煉”,學習西學的目的旨在“歸求反觀”中學。對待西方文化,嚴復強調要“擇其所善者而存之”,甚至認為“新學愈進,則舊學愈昌明,蓋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也”。為此,他試圖在二者建立一個全面的、理性的、平衡的互動關系:“闊視遠想,統新故而視其通,苞中外而計其全。”[10]由此充分體現了嚴復對外來文化的開放包容,也彰顯了他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自信,更體現了他對建構中國近代新型的文化體系的良苦用心。
第一次世界大戰后,嚴復重新審視西方文明,尖銳指出:“西國文明,自今番歐戰,掃地遂盡。”[11]又說:“不佞垂老,親見脂那七年之民國與歐羅巴四年亙未有之血戰,覺彼族三百年之進化,只做到‘利己殺人,寡廉鮮恥’八個字。回觀孔孟之道,真量同天地,澤被寰宇。”[12]他甚至寫道:“往聞吾國腐儒議論謂:‘孔子之道必有大行人類之時。’心竊以為妄語,乃今聽歐美通人議論,漸復同此,彼中研究中土文化之學者,亦日益加眾,學會書樓不一而足,其寶貴中國美術者,蟻聚蜂屯,價值千百往時,即此可知天下潮流之所趨矣。”[13]顯然,在中西方文化的取舍之中,嚴復開始從追慕西方轉向了弘揚傳統,開始拋棄西方文明轉而從中國傳統文化中尋找救國之道,回歸本土的精神價值,進而認為中國儒家文明代表了“天下潮流之所趨”。從此,我們開始有了自己的思考,開始了真正屬于自己的道路探索——這就是尋求一個既高于傳統文化,又高于西方近代文明的更高級的文化模式,一個既體現現代化道路的一般規律又契合本國具體實際的、代表人類社會進化方向的新型模式。對這一模式的探求乃是嚴復之后幾代知識分子努力的核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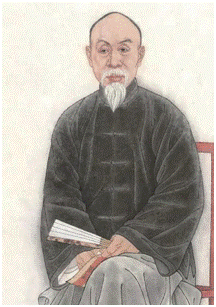
林紓
時與嚴復并稱的閩縣人林紓,是我國翻譯文學的奠基人。林紓從1899年發表第一篇譯作《巴黎茶花女遺事》,至1924年逝世的25年中,翻譯的西洋小說“百數十種”,譯著之豐為中國近代譯界罕見,號稱“譯界之王”,與嚴復并稱譯界“雙子星”。
林紓翻譯的作品源自英、法、美、俄等十幾個國家,其中不乏世界公認的文學名著,如托爾斯泰的《復活》(林譯《心獄》)、狄更斯的《大衛·科波菲爾》(林譯《塊肉余生述》)、塞萬提斯的《唐吉訶德》(林譯《魔俠傳》)、笛福的《魯濱遜漂流記》、斯陀夫人的《黑人吁天錄》、莎士比亞的《亨利四世》等等,不一而足。其所譯小說在清末民初影響之大,被冠以“林譯小說”之稱,成為中國近代文學史上西洋文學經典的代名詞。中國讀者從林譯小說中了解到西方的社會風貌、文學流派、文學大師,打開了中國從事文學者通往世界文學的窗口。林譯小說旨在“冀吾同胞警醒”,成為國人向西方尋找真理的組成部分,對之后的新文學運動有深刻影響。五四時代的作家們,如周作人、郭沫若、冰心、鄭振鐸等,早年都有過一個耽讀“林譯小說”的時期。著名文學家鄭振鐸在1924年11月11日《小說月報》發表《林琴南先生》一文評價道:“他以一個‘古文家’動手去譯歐洲的小說,且稱他們的小說家可以與太史公比肩,這確是很勇敢的很大膽的舉動。自他以后,中國文人,才有以小說家自命的;自他以后才開始了翻譯世界的文學作品的風氣。中國近二十年譯作小說者之多,差不多可以說大都是受林先生的感化與影響的。”[14]文學史家阿英曾說:“他使中國知識階級接近了外國文學,從而認識了不少的第一流的作家,使他們從外國文學里學習,以促進本國文學的發展。”[15]
如果說,嚴、林以譯西書名世,那么,陳季同則以傳漢學著稱。陳季同一生經歷過各種重大的歷史事件,然其影響最大、成就最著者當是在中西文化交流方面。他是中國近代中學西傳第一人,是將中國傳統文化譯介到歐洲的第一人,與辜鴻銘、林語堂三人并稱“福建三杰”。其在歐洲的15年間(1877-1891),正值西強我弱之時,當時西方人眼中的中國形象是落后甚至野蠻的,乃至于“幾乎沒有一個歐洲(包括德國)思想家認為中國社會及文化有可取之處”。[16]陳季同意識到這是閉關鎖國的惡果,認為“錯誤的形成來源于偏見”。為了消解西方人對中國的偏見,讓西方人更好地認識中國人,了解中國文化及其價值,陳季同從1884年開始,一直到歸國后,始終筆耕不輟,用流暢的法文寫了大量著作,向西方人介紹中國文化,并在作品中向西方讀者建構了一個美好而理想的中國形象。可以說,在清末的文人中,沒有人比陳季同在西方更引人注目。巴斯蒂贊揚陳季同是“巴黎文藝沙龍受歡迎的人,他用法語把許多富有魅力的中國民間風俗和文學作品介紹給法國人。這些作品后來由新聞記者富科·德·戴蒙翁編輯出版”。“在他的身上,顯示出那些最早直接深入歐洲社會文化生活的中國人所創造的成果中最奇妙的混合物。”[17]其當時在法國暢銷的著作主要有:《中國人自畫像》《中國戲劇》《中國故事集》《中國人的快樂》《黃人的小說》《黃衣人戲劇》《中國人筆下的巴黎》《吾國》等,在巴黎文學界頗有聲譽,“西國文學之士無不所服”。他翻譯的《聊齋志異》,題為《中國故事》(《中國童話》),是該古典名著最早的法文譯本,也是中國人自己翻譯該著的最初嘗試,法國著名作家法朗士為之寫書評,稱此書“比以前的所有同類翻譯都要忠實得多”。還有,《中國人的快樂》一書中多處提及陳季同家鄉福州的習俗,如:泰山神的游行、福州的溫泉以及清代福州地方文人盛行的折枝詩會。陳季同對折枝詩(又稱“詩鐘”)的緣起及其在福州盛行的情況作了詳盡描述,還例舉了許多詩賽上的佳作加以說明,這不能不說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話。學者錢林森對于陳季同有極為深刻的評價,他說:“作為中國文化和文學的闡釋者,作為中西交通最初的溝通者,陳季同的創造最具價值的部分,不是他直面西方文化時所流露的自豪甚至自夸的情愫,而是他正視西方文化時所擁有的比較意識(如《中國人的戲劇》)、自省意識(如《巴黎人》),以及在移譯、闡述、運用中國文學和文化時所表現的現代意識、創造意識和世界眼光(如《中國人的戲劇》《中國故事集》《黃衫客傳奇》《英勇的愛》)。他在這方面的嘗試和實踐,無疑又擔承著一個先行者的角色,并取得了成功。……當時法國文壇的領軍人物法朗士等,便是通過陳季同和他的作品一窺中國文化的。”[18]
為“開民智”“求變革”,林則徐、嚴復、林紓等人以翻譯為手段,將西方先進的物質文明、社會科學以及文學譯介給國人,域外新知振聾發聵,啟民救國,開啟了近代中國向西方學習的先聲,在中國近代思想文化轉型中發揮著獨特作用。毛澤東同志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指出:“自從1840年鴉片戰爭失敗那時起,先進的中國人,經過千辛萬苦,向西方國家尋找真理。洪秀全、康有為、嚴復和孫中山,代表了在中國共產黨出世以前向西方尋找真理的一派人物。”侯官文化即為中國邁向現代化的歷史進程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資源(啟蒙),為中國的進步潮流打開了閘門,為構建中國特色的現代文化體系作了努力探索。因此,其與中國式現代化有著內在的一致性。
(作者為閩江學院人文學院教授)
注:
[1]【德】馬克思、【德】恩格斯:《共產黨宣言》,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31-32頁。
[2]【日】福澤諭吉著,北京編譯社譯:
《文明論概略》,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年,第9頁。
[3]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上海:東方出版社1996年,第391頁。
[4]陳旭麓:《近代中國的新陳代謝》,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57頁。
[5]《清史稿》卷145《藝文志一》。
[6]【美】張馨保:《林欽差與鴉片戰爭》,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11頁。
[7]賀麟:《嚴復的翻譯》,商務印書館編輯部編:《論嚴復與嚴譯名著》,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年,第31頁。
[8]嚴復:《與梁啟超書》,汪征魯等主編:《嚴復全集》(卷八),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5年,第118頁。
[9]李澤厚:《論嚴復》,《中國近代思想史論》,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年,第262頁。
[10]嚴復:《與〈外交報〉主人書》,汪征魯等主編:《嚴復全集》(卷八),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5年,第202頁。
[11]嚴復:《與熊育钖》(七十三),汪征魯等主編:《嚴復全集》(卷八),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5年,第364頁。
[12]嚴復:《與熊育钖》(七十五),汪征魯等主編:《嚴復全集》(卷八),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5年,第365頁。
[13]嚴復:《與熊育钖》(七十三),汪征魯等編:《嚴復全集》(卷八),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5年,第364頁。
[14]鄭振鐸:《中國文學研究》(下冊),北京:作家出版社2000年,第359頁。
[15]阿英:《晚清小說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82頁。
[16]【德】夏瑞春:《德國思想家論中國·中文版序言》,見《海外中國研究叢書》,南京:江蘇出版社1995年8月第1版,第2頁。
[17]【法】巴斯蒂(M.BastidBrugureie):《清末留歐學生——福州船政局對近代技術的輸入》,陳學恂、田正平編:《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匯編·留學教育》,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版,第276頁。
[18]蔡登山:《情義與隙末:重看晚清人物》“中學西漸的第一人——被歷史遺忘的陳季同”,北京:北京出版社2019年,第189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