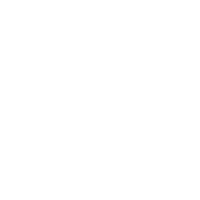西 山 懷 古
哈 雷
1
山水之靈氣在于自然造化之中。奇峰突兀,清流直下,鳥鳴啁啁,草木葳蕤……這些都是好山景必然的元素;若添上清風(fēng)朗月或云霧迷離時(shí),就格外令人流連難忘。記得前幾年登武當(dāng)山,巍巍山峰聳入云霄,奔列峭拔,層巒疊嶂,怪石崢嶸。那峰、那石、那樹,或雄踞如獸,或兀立如屏,或拔地如笏,或伸展如旗,姿態(tài)各異,景象無(wú)限。驀然間,幾縷飄過的輕煙在山岫空壑間繚繞游弋,盡顯仙風(fēng)道骨般之飄逸,如同在夢(mèng)境中見到過的海市蜃樓那般。而你到閩北山區(qū)來,這樣景致的山巒比比皆是,從武夷山脈,到福建最高峰的黃崗山,再到茫蕩山,蒼青色的起伏群山,一座疊著—座,像大海起伏的波濤,無(wú)窮無(wú)盡地延伸到遙遠(yuǎn)的天盡頭。
而山水之魂魄則在于名山與名人的千古對(duì)視,中國(guó)文人大多樂山樂水,一生好入名山游者歷朝歷代接連不絕,又有不少傳說和詩(shī)文留下,就給山水增加了幾多神秘、幾多浪漫、幾多生氣!
有句話說得好,愛上一座城是因?yàn)閻凵狭艘粋€(gè)人,而有時(shí)候愛上一座山也是為了一個(gè)人!
我此次要去造訪的地方是莒口鎮(zhèn)東山村,在武夷山南面,村周圍有兩座大山,東西相峙,間隔八里。西邊的一座名“西山”,高633.9米,總面積兩萬(wàn)余畝,方圓百里。東邊的一座名叫“云谷山”,高999.3米。既不奇崛,更談不上險(xiǎn)峻。閩北在古時(shí)候稱為南蠻之地,地僻人稀,遠(yuǎn)離中原名士賢杰,有名人足跡可循的則少而又少。但卻在八百多年前這兩座山被兩個(gè)人看中,隱居于此多年,遂名聲遠(yuǎn)播。一個(gè)是理學(xué)家朱熹,他深愛云谷山深幽清靜,在此建草房三間,榜曰“晦庵”,隱居山中達(dá)四年之久,“耕山、釣水、養(yǎng)性、讀書、彈琴、鼓缶以詠先王之風(fēng),亦足以樂而忘死矣”。同期,朱熹的得意弟子蔡元定追隨老師復(fù)上西山(蔡元定在拜朱熹為師之前曾在西山筑室讀書)結(jié)廬西山精舍苦讀。兩人遙遙相望,講道山林,磨礪學(xué)問,著書立說。這座本不見經(jīng)傳的小小的西山也因此染上了人文的氣息。
山不在高,有賢則名。當(dāng)年朱熹和蔡元定為了便于聯(lián)絡(luò),雙方約定在各自山頂上建造燈塔,夜間懸燈相望。燈明表示學(xué)習(xí)正常,燈暗則表明遇到疑難問題了,翌日往來論學(xué)解難。蔡元定每到先生處,朱熹必留他數(shù)日,兩人對(duì)榻講論,經(jīng)常通宵達(dá)旦。朱熹女婿黃榦在談及岳父與蔡元定的關(guān)系時(shí)說:“公之來謁朱子,必再數(shù)日,往往通夕對(duì)床不暇寢。”
對(duì)這段八百多年前朱、蔡二位圣賢“每有疑難,則揭燈相望”的典故,當(dāng)?shù)厝艘褵o(wú)所不知,可我在踏入西山之前卻不得而知,聽了十分新鮮,也很受感動(dòng),可見我雖然身居鬧市之中,卻孤陋寡聞,十分汗顏!面對(duì)古代圣賢,一向喜歡調(diào)侃的我們變得幾分恭敬和謙卑,不僅僅對(duì)理學(xué)的敬重,還有一種是對(duì)嚴(yán)謹(jǐn)治學(xué)精神與探尋人類大道的敬重!
2
東山村位于莒口鎮(zhèn)北部,地處西山東北麓,海拔190米,距莒口7.7公里。村委會(huì)所在地在東山。渾頭林只是其中的一個(gè)小自然村。而上西山從渾頭林上是最佳選擇。
我在莒口鎮(zhèn)書記黃洪沙的帶領(lǐng)下進(jìn)到渾頭林村里一棟民居里小憩,黃書記站在院落前的一小塊坪埕上指著對(duì)面一座山說:“那就是西山,像一座臥佛側(cè)躺著,臥視著天空。旁邊那些小山包就像是一串佛珠。”我看西山近在眼前,一朵白云正朝它飄了過來,像漸漸舒展開來的蓮花。西山安詳?shù)靥稍谀抢锏却业脑煸L。
我從渾頭林村沿著蜿蜒曲折的小路騎了一小段摩托車,好久沒有這么悠閑地在村路上騎車了,一路的菜地、翠竹、鳥鳴、稻香,心情一下子也變得舒朗起來。帶著我的是村民賴周明,一路上給我敘述渾頭林他們賴家祖上的故事——沒想到一個(gè)小小自然村也有那么多故事在流傳。
摩托車在半山坡的一間民舍前停了下來。我們準(zhǔn)備棄車徒步上山。這里叫“巖下村”,是上西山的山口,有戶葉姓人家正在爐膛口添柴火,烘烤茶樹菇。我聞到了茶樹菇的香味,禁不住和老鄉(xiāng)攀談起來。原來這里的山民主要副業(yè)收入靠的就是茶樹菇,一年下來每家每戶增收十多萬(wàn)元。
上山的路兩旁盡是茂林修竹和郁郁蔥蔥的大樹。一路上樹林里的空氣特別新鮮,幽雅寧?kù)o,仿佛置身于無(wú)聲世界。烘烤茶樹菇的炊煙裊裊升騰于村子的上空,炊煙帶來了一縷鄉(xiāng)愁般的溫情和感動(dòng)。這里的山連著天,水連著山,山水草木、土墻青瓦、鄉(xiāng)野風(fēng)情……都在淳樸自然的生態(tài)環(huán)境中展開來。路邊鋪滿了松針和雜草,從半山腰望上去,連綿的群山層層依偎,山麓之間的斑斕的冬景醉人心扉,滿地的落葉,山林中紅得耀眼地跳躍出來的楓葉,似在訴說季節(jié)的更替,時(shí)有桂花的清香撲面而來,高大的花梨木仍然濯濯然翠綠,生命的堅(jiān)韌在樹的雄姿中昭然呈現(xiàn)。
在山路上行走半個(gè)多小時(shí),僅見一男一女兩位山民從山上下來,我們停住腳步向他們問路,發(fā)現(xiàn)他們并不是當(dāng)?shù)厝耍瑏碜再F州,因西山松樹繁茂就常年住了下來,靠刮松油賺錢養(yǎng)家,除了春節(jié)回家,一年四季都住在山里。他們也會(huì)采摘蘑菇、蕨類和挖竹筍到山村里去賣。賴周明對(duì)我說,西山的野生紅菇很出名,這里的野生樹林特別適合各種菌類的生長(zhǎng)。沒想到西山還有這么多的物產(chǎn),以它原生態(tài)的方式在為人類做出奉獻(xiàn)。
其實(shí)西山還有另外一條通道可以上山。西山的西邊有座厝橋,叫“龍門橋”。西山的東邊有一座厝橋,叫“化門橋”。因蔡元定家在麻沙,自西向東經(jīng)龍門橋,攀懸崖峭壁,達(dá)西山絕頂。當(dāng)年遇疑難與朱熹切磋理學(xué),就是輒東向下山,過化門橋,到達(dá)云谷的。當(dāng)?shù)匕傩諅鳛槊勒劊瑫r(shí)間久了就成了諺語(yǔ):西山先生“龍門進(jìn),化門出,日在西山,夜在云谷”。老百姓也許不懂得什么理學(xué)大道的,但宋代以來建陽(yáng)“書院林立,講帷相望”,盛況尤甚于春秋曲阜闕里,村民以耕讀持家,對(duì)先賢的尊崇早已是民間的傳統(tǒng)。
不到一個(gè)小時(shí)工夫就到了山頂。西山山體雄偉,四面峻峭,山頂平曠,山中竟然還有兩處農(nóng)田,數(shù)十畝地,農(nóng)作時(shí)村民常常會(huì)到這塊山地來。不知當(dāng)年蔡元定是否也在這里墾荒造地?山間終年霧靄縈繞,古樹參天,泉石清幽,山澗瀑布流水潺潺,逶迤數(shù)十里。史書上說,這里曾經(jīng)還可以走船通舟。山頂有古城墻、練兵場(chǎng)、跑馬場(chǎng)、石切水閘門等,殘存的石城墻高有兩到五米,厚約在三四米間,繞山一圈超過三公里。因城墻內(nèi)外雜樹叢生,難以眺望全貌。城墻內(nèi)還有紗帽巖(俗稱“皇帝帽”)、石鑼、石鼓、石抽屜、天書巖、石寶劍、螺巖、龍井等人文自然景觀。龍井旁就是蔡元定1153年構(gòu)筑的蔡氏書院遺址,山頂坳處是他創(chuàng)建的西山精舍遺址。多年前有愛好西山風(fēng)景之士集資重建精舍,以祀先賢。精舍門前有熱心者余榮貴先生自資筑壩興建西山瑤池,可蓄水供游客乘舟游覽山湖天色。傳說在古代有一位叫羅永的人(百姓稱他為皇帝口乞丐身)一心想當(dāng)皇帝,在山頂上指揮紙人幫他構(gòu)筑城墻、水閘門,以防敵人,每日操練兵馬,以備戰(zhàn)爭(zhēng)。后來夢(mèng)想未成,回鄉(xiāng)帶回兩朵蓮花,把含苞欲放的給了母親,開放得特別熱烈的那一朵給了老婆,從此母親越來越年輕,而老婆越來越老,成為了民間的笑談。而蔡元定在此筑室山頂,忍饑啖薺,刻苦讀書,窮究天理,西山成了大儒之山,西山豐富的物產(chǎn)也頤養(yǎng)了理學(xué)治國(guó)之大家。
走過流水的小橋,漫步山間幽徑,親臨山中瀑布,在紗帽巖邊上一塊西山御書石刻展現(xiàn)在了我的面前。這塊石刻正中刻著“西山”兩個(gè)字,每字一米見方。上款刻書“乙卯賜蔡抗”,下款刻書“寶祐丙辰十月朔,太中大夫參知政事蔡抗刻石”。下款末行刻書“理宗皇帝御書”,字體蒼勁渾樸,刻工講究。是宋理宗為褒揚(yáng)理學(xué),于1255年御書賜予蔡元定孫蔡抗(蔡氏九儒之一),用以表彰蔡元定對(duì)理學(xué)的貢獻(xiàn)。
站在這里,這陡峻的巖石聳立著,仿佛在無(wú)聲地?cái)⑹鲋裁矗址路鹪谄诖裁矗了贾裁?/span>……
3
閩北山區(qū),群山連綿起伏,猶如大海掀動(dòng)的波瀾,呈現(xiàn)出層層疊疊的波峰、浪谷。
西山因?yàn)榈乩矸轿坏木壒剩斐闪霜?dú)特的景觀,即“日出西山,日落東山”,渾頭林村人一直這樣隨天象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山里時(shí)序千年不變,西山是他們祖祖輩輩一日之計(jì)在于晨的仰望和期待。
我站在西山頂時(shí)已是傍晚時(shí)分,太陽(yáng)已斜向了東山村那一片天際,云霧在天際的帷幕中淡露出一點(diǎn)光澤,隨著時(shí)間的轉(zhuǎn)換,一些云朵被染成了緋紅色,在那下面,深藍(lán)與淡灰的山影層層羅列遠(yuǎn)去,直至那抹光澤漸漸擴(kuò)散開來,云幔橫亙?cè)诠鉂膳c山體間,分割出大地與天空的界限。山野的風(fēng)一陣陣吹來,一股寂寥空靈感襲上心頭。
清冷和孤獨(dú)往往會(huì)催生出智慧之花,可是蕓蕓眾生又有誰(shuí)甘于守著一生的清苦與寂靜?!
如果讓你一人住在這樣的地方,現(xiàn)代人做得到嗎?我是一天也做不到的!
但蔡元定做到了!紹興二十三年癸酉(1153年),19歲的蔡元定來到這塊荒蠻的山頂,遠(yuǎn)離塵世的紛擾,構(gòu)筑書院,拿野果野菜充饑,燭火螢燈,苦讀詩(shī)書。與青山綠水為伴,和日月星辰共眠,前前后后長(zhǎng)達(dá)三十八年。他曾賦詩(shī)自詠:“獨(dú)抱韋編過客稀,簞瓢不厭屢空時(shí)。幽然自與庖羲近,春去人間總不知。”又云:“數(shù)櫞茅屋環(huán)流水,布被藜羹飽暖余。不向利中生計(jì)較,肯于名上著功夫。窗前野馬閑來往,天霧浮云自卷舒。窮達(dá)始知皆是命,不妨隨分老樵漁。”就是在這種清凈閑適的環(huán)境中,他遍覽天文、地理、數(shù)學(xué)、禮樂、兵制之書,窮天地之思,達(dá)到了造化精深的學(xué)術(shù)境界。
不過,這人跡罕至的地方,艱難困苦可想而知。當(dāng)時(shí),山中時(shí)有虎豹出沒,夜深人靜之時(shí),山鬼亦來騷擾。起初,山鬼在窗外游蕩,欲嚇唬蔡元定,但他專心致志,不以為意。繼而,山鬼將鮮紅的舌頭伸進(jìn)窗戶,在他的書桌上來回?cái)[動(dòng)。此時(shí)蔡元定正手握朱筆,修改文章,遂順手在山鬼舌頭上寫一“山”字,意思是說,你是個(gè)山鬼,我已知之,不要再吵鬧了。誰(shuí)知,由于蔡元定飽讀圣賢之書,心中正氣沛然,一字既出力重千鈞。山鬼猛然覺得如受電擊,痛得滿山亂竄,通宵哀嚎。次晚,山鬼又到窗前,表示悔過,請(qǐng)求蔡元定解除符咒。蔡元定微笑道,那你再把舌頭伸進(jìn)來吧。待山鬼重新伸進(jìn)舌頭,他揮動(dòng)朱筆,又在上面寫了一個(gè)“山”字。兩“山”相加,組成了一個(gè)“出”字,意思是叫山鬼逃出山去,勿再騷擾。于是,山鬼如釋重負(fù),悄然退卻,再也沒來?yè)v亂。
顯然,這是一個(gè)神話故事。但是,它確確實(shí)實(shí)在當(dāng)?shù)孛耖g流傳著,而且千年不歇。這說明,讀圣賢書,窮萬(wàn)物之理,養(yǎng)浩然之氣,可以驚天地、泣鬼神、繼絕學(xué)、開太平。
綜觀歷史上成大事者都有特別的癖好,或者說都是某一行業(yè)的癡人,古句:“人無(wú)癖不可與交,以其無(wú)深情也;人無(wú)癡不可與交,以其無(wú)真氣也。”有人嗜物,金銀珠寶奇石古玩;有人嗜趣,琴棋書畫詩(shī)酒茶;有人嗜名,忠孝仁義禮智信;有人嗜文,不論多艱深晦澀難懂的學(xué)問他都要一頭撞進(jìn)去……最后一類人是我最佩服的,因?yàn)槲镆椎茫た膳啵嗫汕蟆6ㄓ形模瑢W(xué)問、知識(shí)、思想,才是最大的奢侈品,能成就千古,還能澤被后人,并在歷史上坐實(shí)精神的高地,不是誰(shuí)都能擁有它的。
4
“日落東山”的時(shí)分,我依依不舍地離開了西山。
一個(gè)人行走在黃昏中的遠(yuǎn)山,蒼茫的高空淡出蜿蜒炫目的光,它那么遙遠(yuǎn),卻能迸發(fā)無(wú)窮無(wú)盡的力量和溫暖。就好像有一些美好的人,他們或是已經(jīng)逝去在這茫茫人世里,或是正身處于漫無(wú)邊際的歷史煙塵中;但是,你卻可以通過眼,通過心,去讀去思去感悟去接受他們的饋贈(zèng)——思想、學(xué)問、情懷的激勵(lì)……哪怕黑暗來襲,你也能因此心底透明,勇敢無(wú)畏,激情蕩漾,真切享受自然萬(wàn)物人文歷史之恩澤!
山中不乏大樹參差,枝丫可依靠,樹洞可傾訴,樹葉可遮掩,青苔爬上它的肌膚,藤蔓纏上它的臂膀,小鳥棲息在它的懷抱……西山大儒蔡元定就是這樣一顆大樹,八百多年來,他依然雄踞西山頂,迎風(fēng)而歌,沐陽(yáng)而炫,淡淡然,幽幽中在天地之間透著一股真氣。
自由在高處,思想在高處,寂寞和孤獨(dú)也在高處。
高處不勝寒,即便西山頂已離人世喧囂,山高皇帝遠(yuǎn),但也難逃世俗的羈絆和牽連。
慶元二年丙辰(1196)冬十二月,侍御史沈繼祖上奏誣陷朱熹,并連疏蔡元定,乞“將朱熹褫職罷祠,將蔡元定追送別州編管”。“二十六日旨依,蔡元定編管道州”。三年丁巳(1197)春正月,詔旨頒下,蔡元定自往建寧府治建甌就拘。
“慶元黨禁”名為“學(xué)禁”(時(shí)稱道學(xué)為“偽學(xué)”),實(shí)則一場(chǎng)大規(guī)模政治迫害和思想清洗運(yùn)動(dòng)。理學(xué)集大成者朱熹被定為“偽學(xué)魁首”去職罷祠。而蔡元定一生不涉仕途,不干利祿,潛心著書立說,也被列入“黑名單”,是因?yàn)樗侵祆渥钣H密的朋友兼門生,他就是以布衣身份被“編管道州”的士人。因此,蔡元定以“佐熹為妖”的罪名,貶謫三千里外的道州監(jiān)管。
蔡元定帶著兒子蔡沉,還有門生邱崇、劉砥陪侍,扙履步向湖南道州。年過花甲的儒生,三千里之遙的僻遠(yuǎn)之地,途中顛沛流離、備極辛苦,“杖履同其子沉行三千里,腳為流血,無(wú)幾微見言面”。蔡元定被編管道州,仍與朱熹有書信往來。最后一封,蔡元定在貶所病危,臨終寫信給朱熹:“定辱先生不棄,四十余年隨遇,未嘗不在左右,數(shù)窮命薄,聽教不終……天下未必?zé)o人才,但師道不立為可憂矣。”這成為蔡元定的絕筆,書畢《別晦庵書》即逝,是時(shí)慶元四年(1198年)八月初九,64歲。
蔡元定的去世,使得朱熹如傷手足,痛心疾首,三撰祭文以哭。南宋大臣、理學(xué)家劉爚在《西山先生蔡公墓志銘》中曰:西山千仞兮清潭一曲,先生永存兮過者其肅。
站在長(zhǎng)埂村的化龍橋上,回首望一望云霧繚繞的西山,再騁目云谷山,留在內(nèi)心深處的依然是對(duì)二位圣賢的景仰,當(dāng)然還有對(duì)歷史風(fēng)云中的人和事的悲涼和感慨,耳邊回響起了朱熹《望西山》的句子——
風(fēng)月平生意,江湖自在身。
年華供轉(zhuǎn)徙,眼界得清新。
試問西山雨,何如湘水春。
悠然一長(zhǎng)嘯,絕妙兩無(wú)倫。
云霞漸漸熄滅了它的熱情,夜嵐翻卷過了一層層山林,漫向村莊。西山云谷若隱若現(xiàn),這兩座山依偎在閩北群山之間,雖然它們聲名不能與三山五岳相比肩,但因?yàn)橛辛四纤蝺晌淮笕宓淖鸫妫粝虑Ч偶言挘陡行牢俊=?yáng)是一塊文化的厚土,這里的每一片土地都溫?zé)嶂鴼v史的勝跡。建陽(yáng)籍作家王宏甲說:“寫到家鄉(xiāng),我的筆都會(huì)溫暖起來。我不知怎樣來描述這種溫暖給予我的恩惠,但我知道,我常因家鄉(xiāng)而感到豐厚的擁有。”我想這種豐厚不僅僅在大山物產(chǎn)生生不息的賜予,更在于歷史人文綿綿不絕的流傳。
回縣城的路蜿蜒起伏,車燈射出的光像一束潑出去的顏料,路面上兩邊斑斕的樹葉描摹著山景。冬天的閩北是豐富的,紅的、黃的、綠的、淡黃的、枯黃的,各種顏色的樹葉密密匝匝簇?fù)怼⒍逊e、搖曳,樹影橫空,卻又各自矜持,許是得了仙山靈氣,浸染了出家的淡泊與深厚、人的寧?kù)o與寬闊。
(本文原載于《走進(jìn)建陽(yá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