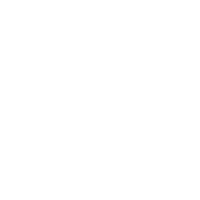·“海絲文化與福建”百題·
(漳州卷)122.以海為生,月港人的生活習俗
1.月港人的“海國”生計
明代王世懋指出,漳州人“以舶海為恒產”。王起宗認為,漳州“海國也”,“其民畢力汗邪,不足供數口。歲張艅艎,赴遠夷為外市,而諸夷遂如漳窔奧間物云”。([明]張燮著,謝方點校:《東西洋考》之《序》,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13頁)月港靠海,當地人自然能夠以海為生。時人云:“閩為岐海,而諸邑于海最近者莫若澄”,“邑人以海為生活,小艇漁歌,每截流而橫絕島;巨航寶貨,羌趁舶而狎賈胡”。([明]梁兆陽修,蔡國禎、張燮等纂:《(崇禎)海澄縣志》卷一《輿地志·形勝》,書目文獻出版社影印崇禎六年(1633)刻本1992年版,第329)明末海澄人詹海章《宴海樓賦》云:“斥鹵多而沃腴少,居民因海以為田,取給于魚蝦蚌蛤而為利,商賈多逐末以謀生,舟車輻輳而奔駛。”由此可見,月港民眾有海利之便,除了農民,多以做漁民和海商為主。
《嘉靖龍溪縣志》云:“海鄉之民多業漁,往往浮家泛宅。其目有罾艚、網艚、畟艚之類,皆為機網,以取魚海潮上。漁舟西歸如亂葉,人多于魚,利之厚薄可知矣。”即月港近海漁民太多,捕魚獲利較小。而月港海商的情況不一樣。《嘉靖龍溪縣志》云:“商人貿遷,多以巨舶行海道,所獲之利頗厚。時有颶風之險,亦冒為之。”([明]劉天授修,林魁纂:《嘉靖龍溪縣志》卷一《地理》,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第32冊,上海古籍書店1981年影印本,本卷第16頁)他們為了豐厚的利益,制造巨大海船,不惜冒颶風狂浪之險去海外貿易。而造一艘遠洋大船成本較高,漳州沿海民眾往往集資造船,“裝土產,徑望東、西洋而去,與海島諸夷相貿易”。([清]顧炎武撰,黃珅等校點:《天下郡國利病書》,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3091頁)這是漳州府沿海民眾的常見風氣。如嘉靖二十六年(1547),漳州月港多家海商“造過洋大船,往來暹羅、佛郎機諸國,通易貨物”;同時,漳州海商與泉州海商還與日本海商貿易往來,“倭亦以巨航至”。嘉靖中,“有佛郎機船載貨泊浯嶼,漳龍溪八九都民及泉之賈人往貿易焉。巡海道至,發兵攻夷船,而販者不止”。其中就有龍溪縣八、九都海商張維、洪迪珍等24人,共集資建造一至兩艘遠洋大船,“接濟番船”。不久,張維、洪迪珍等24人干脆號稱“二十四將”,“官兵不能制”。([清]顧炎武撰,黃珅等校點:《天下郡國利病書》,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2968—3106頁)
2.月港海商的海洋知識
自唐代以來,漳州沿海商民逐漸積累了豐富的海洋知識,包括潮汐知識、可靠的航海經驗和海洋氣候經驗。
首先看漳州出海商民對潮汐的經驗總結。漳州府龍溪縣正德八年(1513)的潮汐記錄:
漳州府所領六縣,唯龍溪、漳浦二縣近海,故潮汐入焉。龍溪縣潮由濠門、海滄二夾港入,分為三派:一派入柳營江,至北溪止;一派入浮宮,至南溪止;一派入福河,繞郡治南,過通津門,至西溪止。……所謂潮汐者,晝潮以朝至,故名潮;夜潮以夕至,故名汐。總而言之,皆謂之潮也。其為消長也,各應時而至,如初一、初二晝潮以卯時長、午時消,夜潮以辰時長、子時消;至初四、初五,則晝潮以辰時長、未時消,夜潮以戌時長、丑時消,率兩日而移一時。其為大小也,各應候而至,如每月初三日潮大,初十日潮小,十八日潮大,二十五日潮小,率八日而一變。至于每歲,則卯酉二月皆大,而酉月為尤大。夫潮候在天地間應時應候,毫發不爽。([明]陳洪謨修:《(正德)大明漳州府志》卷七《山川志·龍溪縣》,廈門大學出版社影印明正德八年(1513)刻本2012年版,第443—445頁)
這個記錄包含正德八年(1513)龍溪縣倒灌入江潮汐的地點、數量,以及每月潮汐的具體時間。這是現有文獻中有關龍溪縣潮汐的最早記載。
《嘉靖龍溪縣志》對漳州沿海的潮汐進行了進一步總結:
候潮之法,以太陰每日所躔天盤子、午、卯、酉之位而定其消長。月臨于午則為長之極,歷未及申、酉則極消;消極復長,以至于子,又為長之極;自是至卯而消,復至于午而極盛。此其大較也。然月順天右行,積三十日,始一周天,每日臨子、午、卯、酉四位時有先后,故潮因之亦有晝夜、早暮之不同云。
初一、初二、十六、十七,潮至在巳、亥二時;初三、初四、初五、十八、十九、二十,潮至在子、午二時;初六、二十一、潮至在未、丑二時;初七、初八、初九、初十、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潮至在申、寅二時;十一、十二、二十六、二十七,潮至在卯、酉二時;十三、十四、十五、二十八、二十九、三十,潮至在辰、戌二時。
右分為六節,應月消長。月行雖有常度,大率朔望前后則行疾,至上下弦則行稍緩。月行疾則度嬴而潮盛,月行緩則度縮而潮微。水陰氣月為陰之母,其相應如此。([明]劉天授修,林魁纂:《嘉靖龍溪縣志》卷一《地理》,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1965年影印寧波天一閣藏明嘉靖刻本,本卷第22—23頁)
《嘉靖龍溪縣志》編于嘉靖十四年(1535),距離《(正德)大明漳州府志》編定的正德八年(1513)才2O余年。嘉靖十四年龍溪縣候潮法總結得比較清晰,主要以太陰天盤四位法為基本理論。
崇禎六年(1633)刻印的《海澄縣志》也有記載:
(前略)漳人之候潮也,夜則以月,晝則以時,于指掌中從日起時,順數三位,長半滿,退半盡,以六字操之,無毫發爽。海上漁者,于海嘯則知風,海動則知雨。潮退則出,潮長則歸。其方言云:“初一、十五,潮滿正午;初八、廿三,滿在早晚;初十、廿五,日暮潮平。”又云:“月上水翻,流月斜水,半月落水。汐盡,潮則呼曰南流上,汐則呼曰北流落。”……至海外之潮已平,而內溪猶長,則氣盛而未收。俗所云“港尾水”,又云“回流水”是也。海口以潮平為度,其穿達支流,仍以百里而緩……論曰:澄昔故荒藪也。建邑以來,頓稱望國。因天因地,存乎其人;王氣所鐘,自覺二儀永奠、三辰重朗者焉。觀象度形,前借斯具;高丘遠浦,備加采擷。綺望咸羅,試展卷而思長。維照夜殊勝于燭燎,成圖無假于聚米矣。([明]梁兆陽修,蔡國禎、張燮等纂:《(崇禎)海澄縣志》卷一《輿地志·形勝》,書目文獻出版社影印崇禎六年(1633)刻本1992年版,第330—331頁)
這說明,至明朝末年,月港人的候潮法更為便利,可以在指掌細數,民間總結更為詳盡。至于“駕舟洋海”,商人們不僅憑風力、潮信來判斷,也可以參照月亮、北斗來夜航。這反映出漳州海商更加豐富的遠洋航行經驗。
3.航海經驗總結
漳州海商常年以海為家,航行于海洋之間,如“比歲海濱人視越販為常事”“夫越販起于富人射利”“舶主土豪……走波濤中”,與佛郎機等諸夷及南番諸國交相往來。([清]顧炎武撰,黃珅等校點:《天下郡國利病書》,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3105頁)經過數百年乃至千余年的探索,漳州航海者對海洋氣候、海道、航行技巧、沿線諸國風土人情都有比較深入的了解。《(崇禎)海澄縣志》云:“至于駕舟洋海,雖憑風力,亦視潮信,以定向往。或晦夜無月,唯瞻北斗為度。”([明]梁兆陽修,蔡國禎、張燮等纂:《(崇禎)海澄縣志》卷一《輿地志·形勝》,書目文獻出版社影印崇禎六年(1633)刻本1992年版,第331頁)
明末漳州府龍溪縣人張燮《東西洋考》對海澄海商的航海經難有詳細總結:
海門以出,洄沫粘天,奔濤接漢,無復崖埃可尋,村落可志,驛程可計也。長年三老鼔枻揚帆,截流橫波,獨恃指南針為導引。或單用,或指兩間,憑其所向,蕩舟以行。如欲度道里遠近多少,準一晝夜風利所至為十更。約行幾更,可到某處。又沉繩水底,打量某處水深淺幾托(方言謂長如兩手分開者為一托)。賴此暗中摸索,可周知某洋島所在,與某處礁險宜防。或風濤所遭,容多易位;至風靜濤落,駕轉猶故。循習既久,如走平原,蓋目中有成算也。([明]張燮著,謝方點校:《東西洋考》卷九《舟師考》,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170頁)
張燮的《東西洋考》可以說是明末海外貿易的“月港通商指南”。他明確指出,遠洋航行主要依靠指南針,已經發展出單針與雙針導航,并以“更”作為航程計算單位,以“托”為海洋水文測量單位。這樣,月港的海商就能比較充分地掌握以月港為中心的17世紀西太平洋貿易航路信息,掌握了遠洋航行導航工具、航程及其計算方法、定位方法等。當然,因為《東西洋考》是張燮當時應海澄縣令陶鎔、漳州府督餉館別駕王起宗之邀而作,屬于半官方身份,能夠充分搜集到各種信息。他“間采于邸報所抄傳傳,與故老所誦述,下及估客、舟人,亦多借資”,多是一手資料,比較真實可靠。
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也有對漳州海商航海經驗的記載:
(漳州)商舶,則土著民醵錢造舟,裝土產,徑望東、西洋而去,與海島諸夷相貿易。其出有時,其歸有候。廣洋巨浸,船一開帆,四望唯天水相粘無畔岸,而海人習知海道者,率用指南針(即羅經)為其導向。相傳有《航海針經》,針或單用,或指兩辰間。以前知某洋島所在,約更時當行水路幾許,打量水深淺幾托(方言“幾仞”為“幾托”),海中島嶼作何狀,某洋礁險宜慎,或風云氣候不常,以何法趨避之。異時海販船十損二三,及循習于常所往來,舟無恙若安瀾焉。蓋海濱民射利精如此。([清]顧炎武撰,黃珅等校點:《天下郡國利病書》,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3091頁)
顧炎武所載內容指出,漳州海商熟悉海洋,其航海能夠“出有時”而“歸有候”。航海之人熟悉前往各洋的海道。他們航海技巧嫻熟,有羅盤、指南針指引其前進方向。尤其是他們總結航海經驗,制作了《航海針經》,羅盤、指南針可以是單針或兩辰針,在到達某個蕃國海港之前,就能夠知道其方向,知道航程大約是幾更,當地水文情況如何,周圍有什么特殊形狀的島嶼或洋礁險灘,或遇到惡劣氣候時可以用什么方法來化解等,即如《順風相送》《渡海方程》等。
關于《航海針經》,這里再稍作補充。航海針經,或簡稱為《針經》,或類似于近年發現的《針路簿》或《更路簿》,應相當于現在的航海日志,是航海人多年航路的記載和經驗總結。張燮指出:“舶人舊有航海《針經》,皆俚俗未易辨說,余為稍譯而文之。其有故實可書者,為鋪飾之。渠原載針路,每國各自為障子,不勝破碎,且參錯不相聯,余為镕成一片。沿途直敘,中有迂路入某港者,則書從此分途軋入某國,其后又從正路提頭直敘向前,其再值迂路亦如之。”(明]張燮著,謝方點校:《東西洋考》之《凡例》,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20頁)張燮這段話是《東西洋考。凡例》中的一部分,主要是說明航海針經一般每艘船都有,記載不同,不同地域商人的俚俗用語也各異,很大一部分只是記載去某個南洋蕃國的航線。張燮把同一條航線可以到達的國家或港口串聯起來,才有張燮《東西洋考》第九卷《舟師考》。就此而言,張燮可以說是明末中國遠洋航路經驗總結的集大成者。